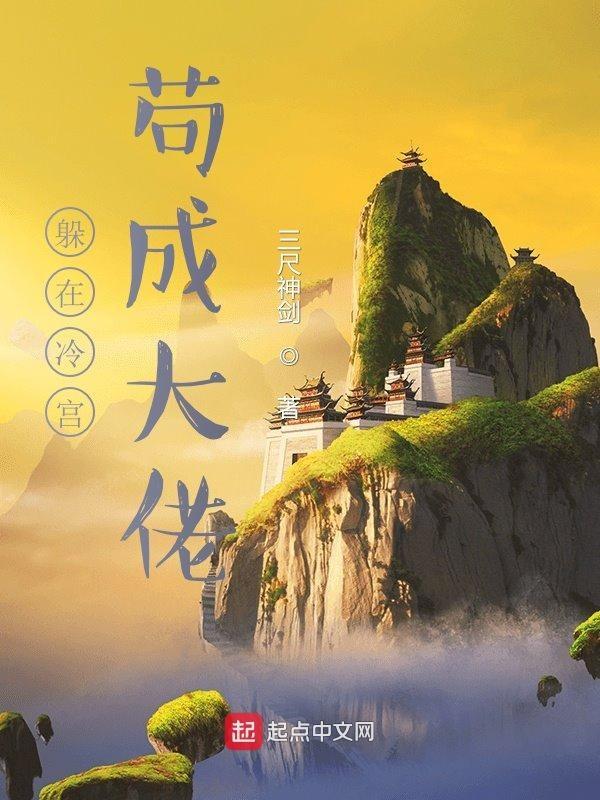我的书库>永安遗事 > 秋尽之后(第1页)
秋尽之后(第1页)
洛京的秋天总是无比漫长,却又不知在何时猝然结束,当人反应过来时,一场绵绵絮絮的雪已经落下来了。
雪下得不大,落在地上薄薄一层,脚一踩上去就化成了泥淖的脏水。
钟含章要堆雪人玩,便不许人从正堂前的院子里走。正堂前的地儿最空旷,地面铺着青石板,雪也干净。环翠守在正堂前,忠实地履行着娘子的命令。
钟衢要出门去府衙,环翠嬉笑着脸恭恭敬敬地拦住了太尉大人:“老爷,娘子说了,这块地谁都踩不得,您老换条路吧?”
钟衢愤然拂袖道:“真是成何体统,我府上还有我走不得的路!皇宫里的地倒是大着呢,她怎么不去把宫里的地也拦起来!”
环翠知道老爷的脾性,他从不会对钟含章真的大动肝火,仍旧笑嘻嘻道:“娘子也是见到今岁第一场雪新鲜,要堆雪人玩呢。等老爷回来就能看到娘子堆的雪人了。”
钟衢冷哼一声:“我多大的人了,还稀罕看她小女儿家家的玩意?”话虽这么说,太尉大人还是屈尊降贵地绕路从侧门出去了。
环翠见地上的雪渐渐积起来有寸许,估摸着扫一扫也能堆一个雪人出来了,便欢天喜地地站起来准备去叫自家娘子。
她刚站起来,便见曾泉步履匆匆地进来,直直地穿过正堂前的院子而来。环翠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又不便冲过去抓他,只好在堂前大叫:“曾泉你不要命了!老爷都没从这走,你比老爷还尊贵吗!娘子不杀了你,我也要剁了你剐了你!"
曾泉对环翠的话听而不闻。他快步走到正堂,见环翠还在大喊大叫,连忙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姑奶奶,你可低声些吧。我哪里能和老爷比,但比老爷还尊贵的人来了,你不能让长公主殿下的人也走侧门吧!”
环翠顿时安静了下来,她瞪圆了眼睛,含糊不清道:“长公主府上的人怎么来了?”
曾泉见环翠不再大叫,便放下了捂着她嘴的手:“是来找咱们娘子的,我爹已经去迎着往正堂来了,你赶快去请娘子出来吧!”
环翠应声后便连忙朝后宅跑去。
钟含章出来时,管家曾叔已经将客人迎到了正堂看茶。曾叔是钟府的老人,极受钟衢的信任,他待人接物无不妥帖。因此,虽只是钟府仆人作陪,长公主府上的人倒也对他和气有加。
一宫装女子虚虚地坐于堂上最末端的椅子上,见钟含章过来,她从容起身,敛衽行礼道:“奴莲月见过钟娘子。”
钟含章轻轻扶起她:“何必多礼,不知莲月姑姑所来何事?”
莲月笑道:“自诗会一别,公主颇为记挂娘子,今日遣奴来,便是接娘子过府一叙。”
钟含章面上带着笑意,心里却生出疑虑:她和长公主的交情什么时候已经到需要特意派人来接她去公主府叙旧的程度了?
她神色不变,嘴角带着恰到好处的荣幸备至的笑意:“劳长公主记挂,含章惶恐难安。我这就命人备马车,前去拜望殿下。”
曾叔闻言已经示意曾泉下去准备车马出门,莲月却笑盈盈地摆了摆手:“钟娘子不必费神,公主吩咐过,娘子坐公主府的马车便好。”
钟含章心下疑惑更甚:她和孟宜周的交情也没有坏到孟宜周要给她摆一道鸿门宴的地步吧?
钟含章只道:“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她侧头对环翠道:“你去将我那件紫狐氅裘拿来。”
环翠会意后,应声离开。
道上雪融化后凝结成冰,马车不敢行驶太快。钟含章揭开车帘,她看出马车并不是往公主府的方向走的。
钟含章道:“这车夫莫不是新来的,连回公主府的路也记不清?”
莲月依旧笑盈盈的:“娘子说笑了,公主府上的人从不敢犯错。”
钟含章没有理会她,她依旧看着窗外,一抹青色的身影时隐时现地跟着马车。
她知道江平楼是故意让自己看见他的,一时心安下来。
马车终于停了下来。
钟含章走下车来,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座黑沉沉的建筑,如一头匍匐在帝都阴影里的巨兽。
这地方墙体极高,仰头难见其顶,仿佛硬生生地要将天空都撕扯下一块来。墙壁上不见半扇像样的窗户,只有几道狭窄的缝隙,透不出光,只像是一道道凝视着外界的、毫无感情的黑色视线。那两扇巨大的玄铁门紧闭着,上面铸着狰狞的狴犴兽首,铜环已被磨得幽亮,冷得不带一丝人气。
一股混合着铁锈、陈旧血腥和某种诡异腐败气息的阴风,无孔不入地从门缝、从墙隙中丝丝缕缕地渗出来,缠绕在人的鼻端。钟含章不禁微微地打了一个寒颤,她有些悲哀地想,这世上固然所有人都畏惧此地,但位高权重的人想必畏惧更甚。
她对莲月道:“不是要去公主府吗,怎么来诏狱了?”
莲月笑道:“公主确实是派奴来请钟娘子叙旧的,但与钟娘子叙旧之人却不是公主。娘子不必惊慌,那个人不过临死前有几句话想和娘子说说罢了。”
一身穿青灰色交领袍服的官员早已候在了门口。见钟含章和莲月下车,他连忙迎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