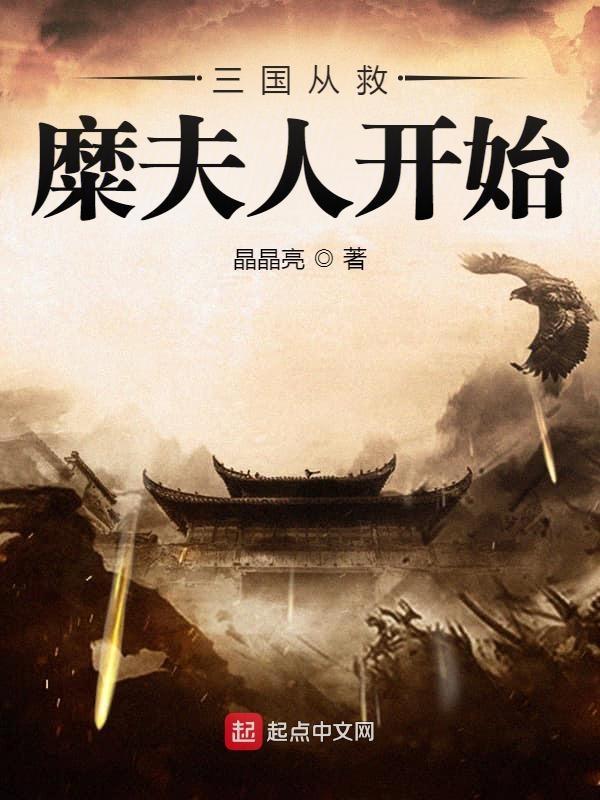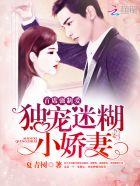我的书库>从豪门大小姐手中领养自己 > 6065(第34页)
6065(第34页)
只说她记得的。
她小学的六年,每一天。
都是自己上下学的。
有些回忆慢慢苏醒。
***
六岁的安迟叙踢遍了上学路上的石子。
十二岁的安迟叙已经能精准叫出每一个石子的名字。
有时她会悄悄带一颗回家。把它擦洗干净,写作业时对着它讲话。
她不是能说会道的孩子,于是交流的方式变成了“传纸条”。
安迟叙写过一张一张的纸条,垒起来能堆几个作业本。
童年最好的朋友是那颗太不起眼所以没被安予笙丢掉的石头。
有时她会把学校里的石子丢到上学路上,给她觉得孤单的石头作伴。
有时她会关照缝隙里的蜗牛。有的小朋友天生怕虫,安迟叙却没有虫子的概念。
六岁的年纪对什么小生命都好奇。好奇这带着壳的小玩意怎么吃饭睡觉,壳是不是它们的家,为什么和自己不一样。
有时她会把落在墙边的藤蔓拽下来。她好奇,却没有成年人会有的敬畏心。
藤蔓摘了就是死了,六岁的小安迟叙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她的第一次死亡教育在高三。由晏辞微领着她,听完一整首萨满的歌。
或许是接受死亡教育太晚。她至今对生死都没有太多敬畏,反而有隐秘的期待,见不得光的悸动。
有时小安迟叙又会把作业塞到她的石头朋友中间。
她不理解为什么她的朋友不能帮她写,干脆把不想写的麻烦撕了扔在路上。
安予笙知道这件事。老师批评安迟叙,找到安予笙时,安予笙还很惊奇。
安迟叙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乖孩子。上课不哭不闹,不和同桌说话,更不会像有些小孩一样站起来嬉闹。
回家也很乖,每天准时出门,准时到家,吃两口饭就去书桌坐一晚上。安予笙还以为她在写作业。
这样的安迟叙是乖孩子中的乖孩子。怎么可能把作业扔了。
“你作业呢?昨晚不是做了吗?快拿出来给老师啊。”安予笙拽了拽手里的安迟叙。
好像她不是她的女儿,是一只随意蹂。躏的布娃娃。
“喂石头了。”安迟叙说的很小声,好像在心虚。
她太矮了,还没有达到一年级的平均身高。老师也看不见她的眼。
如果有谁看见就会知道,那绝不是心虚。
是冷漠。
这样的眼神不该出现在一年级小孩的脸上。
只是谁会去直视一个从来都很乖巧的孩子?
“没写?安迟叙,怎么能不写作业呢?”安予笙都没问安迟叙的话是什么意思。
她们就算是不亲,也是母女。安予笙最能听懂安迟叙的话。
老师都还没太明白,就见安予笙跟她道歉。
“不好意思啊,我工作太忙了,对她有点疏忽了。之后会好好管的。”
所谓好好管,也就是安予笙守了安迟叙做作业一个星期。
其中还有两天是安迟叙的妈妈守的。
安迟叙的石头当然被丢了几块。但没关系,安迟叙还有更多的石头朋友。她孜孜不倦的往家里捡。
终于到十二岁那年,没有人再丢她的石头,她也对石头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