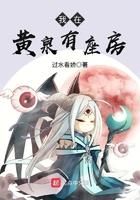我的书库>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 强矢困局(第1页)
强矢困局(第1页)
前线传来的紧急军情,如同一道新的催命符,将刚刚平息内部纷争的将作监再次推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西夏人的轻型复合盾,显然采用了新的材料和工艺,有效抵御了宋军现役箭矢的穿透,这无疑是对大宋军工体系的一次严峻考验。
枢密院的命令措辞严厉,要求将作监与军器监(少府监下属,负责部分军械)通力合作,限期拿出强矢方案,以解前线燃眉之急。
压力再次层层传递,最终落到了赵楷的肩上。
“强矢……”赵楷看着军报上对敌盾的描述(皮革、毡布、薄木片多层复合,轻便坚韧),眉头紧锁。要破此种盾,无非两条路:一是提升箭矢初速(需要更强力的弓弩),二是提升箭镞的穿透力(需要更硬、更重、更锋利的箭镞)。
改进弓弩涉及整体结构,周期长,难度大,远水难救近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改进箭镞。
然而,箭镞的改进,立刻触及了赵楷一直以来最深切的痛处——材料瓶颈。
将作监现有的制式箭镞,多采用中低碳钢锻打淬火而成,硬度有限,韧性尚可,对付无甲或轻甲目标足够,但面对复合多层防护,就显得力不从心。要提高穿透力,就需要更高碳含量、更高硬度的钢材,同时还要保证一定的韧性,避免撞击硬物时碎裂。
“高碳钢……淬火工艺……”赵楷喃喃自语,感到一阵头疼。
这不是设计问题,也不是工艺规程问题,这是材料学和热处理的硬核难题!完全超出了他前世机械工程师的知识范畴,更是这个时代工匠们依靠经验摸索、极不稳定的领域。
他立刻召集将作监最好的铁匠和热处理工匠(如果有的话)商讨。
老师傅们听了要求,纷纷摇头。
“赵先生,不是俺们不尽力,这铁……它就不是那块料!”一位老铁匠摊手道,“官中拨付的铁料,杂质多,碳星子(碳含量)不稳,时高时低!打出来的镞,淬火时不是软就是脆!难啊!”
“淬火更是看天吃饭!”另一位负责热处理的工匠愁眉苦脸,“全凭眼看火色,手感水温!一炉料,淬出来能有七八成合用,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了!要批批都硬,还要不脆?这……这没法子保证啊!”
情况比赵楷想象的还要糟糕。原材料的质量波动巨大,热处理工艺全凭经验,极度不稳定。所谓的“标准化”生产,在源头的材料环节就几乎失效了!
“能不能精选铁料?或者……我们自己炼?”赵楷不甘心地问。
老铁匠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自己炼?赵先生,那是工部虞衡清吏司和各地铁监的差事!将作监只有打铁的炉子,没有炼铁的高炉啊!精选?好料都紧着刀剑甲胄,轮到箭镞的,能是啥好货?”
现实如同一盆冷水,浇得赵楷透心凉。他空有“标准化”的理念和些许精度控制的手段,却倒在了最基础的工业母材关上。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他没有时间沮丧。军令如山,必须想办法。
他首先尝试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进行优化。他让铁匠对入库的铁料进行更严格的筛选,凭经验挑选那些色泽、断口看起来碳含量稍高的料块。然后,他试图对淬火工艺进行“标准化”改良。
没有温度计,他让人在炉旁立一根铁棍,观察其受热变色的程度,结合老师傅的“樱桃红”、“橘黄红”等经验口诀,划定一个大概的加热温度范围(极不准确)。
没有恒温淬火液,他尝试用不同的介质——水、油(菜籽油、豆油)、甚至盐水、尿(据说能改变冷却速度)……记录下每种介质淬火后的大致硬度和韧性表现(全靠手感敲击和简易弯曲测试)。
他还异想天开地尝试了表面渗碳——将箭镞埋入木炭粉中加热,试图让碳元素渗入表面,增加硬度。结果不是没效果,就是渗碳不均,甚至把箭镞烧坏了。
过程混乱,数据粗糙,结果波动极大。偶尔能出一两批性能不错的箭镞,但根本无法稳定复制。废品率居高不下,生产效率极其低下。
工部派来的“督导”(钱主事虽然暂时失势,但工部换了人来)冷眼旁观,不时冷嘲热讽:“赵先生的‘标准化’,看来也并非万能啊?离了巧匠手感,便玩不转了?”
赵楷气得牙痒痒,却无力反驳。材料科学的鸿沟,不是靠管理方法和简陋工具就能轻易跨越的。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狄明月又带来了新的消息。她通过狄家的关系,从军器监那边打听到,少府监也在攻关强矢,他们的思路是——重箭。
“军器监那帮家伙,说既然穿不透,就加大分量,用重箭硬砸!”狄明月撇撇嘴,“他们在试三棱破甲重箭,箭镞加大加厚,用最好的铁料,就是死重,射不远,弓弩手抱怨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