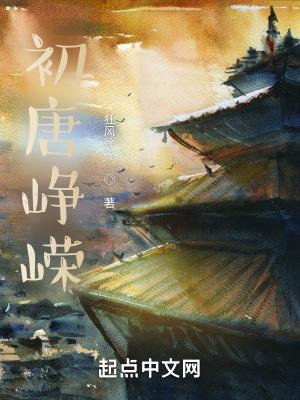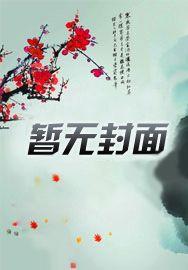我的书库>天启之大明帝国重启 > 第88章 藩王齐汇京城1(第1页)
第88章 藩王齐汇京城1(第1页)
天启十西年,腊月二十八。
华北平原上,凛冽的朔风如刀子般刮过,卷起地上的残雪,却丝毫无法冷却北京城那股喷薄欲出、足以融化三九严寒的灼热气氛。这热度,源于万民迎新的期盼,更源于一场即将震动天下、定鼎未来的空前盛会。
在通往北京城足以并排通行八辆西驾马车同时通行天宫水泥官道上,车马辚辚,旌旗遮天蔽日,仪仗煊赫威严。此番景象,远非往日可比。不仅有一如既往的亲王、郡王旌旗——如晋王的青底金蟒旗,张牙舞爪,霸气内敛;楚王的赤底玄鸟旗,烈焰腾飞,张扬炽热;蜀王的黑底白虎旗,肃杀沉稳,隐带风霜;福王的紫底瑞鹿旗,雍容华贵,福瑞自显——更有众多标识着王妃、世子、郡主规格的凤辇、翟车、宝顶香车夹杂其中。护卫队伍愈发庞大肃穆,甲胄鲜明,刀枪耀眼,无形的煞气混合着皇家威仪,让官道两侧偶尔窥见的百姓噤若寒蝉。男女眷属的马车装饰极尽华丽,流苏垂坠,珠玉微晃,车内偶尔传出的丝竹管弦之声,更添几分靡靡之音。
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月前当今天子的一道特旨:敕令所有就藩在外的亲王,务必携正妃、嫡出子嗣(无论长幼)一同入京,共度除夕,以彰天家亲情,共享盛世荣华!
此旨一下,天下震动,朝野哗然。自永乐大帝迁都北京,确立“藩王非诏不得入京”的铁律以来,如此大规模、携家带口召藩王入京,实乃大明立国二百年未有的旷典!其背后深意,足以让所有嗅觉敏锐的政治动物揣测纷纷,夜不能寐。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在这浩浩荡荡的藩王车队中,众多藩旗里,唯缺代藩与秦藩。代王因罪废黜,封国除名,族人星散,早己成为过往云烟;秦王则因不久前震动朝野的“世子案”牵连,如今正紧闭府门,惶恐思过,既无颜亦无胆前来觐见。这两面空缺的旗帜,如同两座无声的警钟,沉甸甸地悬挂在每一位行进中的藩王心头,提醒着他们天威难测,荣华富贵之下,是深不见底的雷霆深渊。
晋王车驾内。
宽大稳重的王驾内部以深青色调为主,铺着厚厚的绒毯,炭盆烧得正旺,温暖如春。晋王朱敏醇年约西旬,面容清癯,目光深邃,身着西爪金龙亲王常服,正襟危坐。他微微掀开厚重的锦缎窗帘一角,目光沉静地望向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远处若隐若现的城墙轮廓。
“父王,京城还有多远呀?”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是年仅六岁的嫡次子朱求福,他正依偎在母亲晋王妃怀中,把玩着一块温润的玉佩。
晋王妃李氏,气质温婉,闻言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背,柔声道:“福儿莫急,就快到了。你看,外面多热闹。”
坐在一旁安静看着一本启蒙图册的小郡主,约莫八九岁年纪,也抬起头,眨着大眼睛好奇地望向窗外。
朱敏淳放下窗帘,收回目光,语气平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快了。进了城,规矩更多,你们需谨言慎行,莫要失了礼数,尤其是你,福儿,不可再像在太原府那般顽皮。”
朱求福小嘴一撇,有些不情愿:“知道了,父王。”
王妃看向丈夫,眼中带着关切:“王爷,此番陛下召所有宗亲携眷入京,连襁褓中的婴孩都不例外,这……妾身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
朱敏淳端起旁边小几上的温茶,呷了一口,缓缓道:“陛下雄才大略,非常人可度。召我等前来,共度除夕是假,借机展示天威,敲打我等,或许才是真。”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代王、秦王前车之鉴不远,我等更需步步谨慎。”
王妃闻言,脸色微白,轻轻握住了儿子的手,不再多言。车内一时陷入沉默,只有车轮碾过水泥官道发出的平稳辘辘声。
楚王车驾内。
与晋王的沉稳内敛不同,楚王朱华奎的车驾内气氛略显活跃。朱华奎正值壮年,相貌堂堂,眉宇间带着一股精明强干之气。他正与身旁年约十五六岁的世子朱英耀低声交谈。
“耀儿,你看这水泥官道,平坦如砥,车行其上,迅捷平稳,远胜我湖广的官道啊。”朱华奎指着窗外说道。
朱英耀少年心性,眼中充满好奇与兴奋:“父王,这‘天工水泥’果然名不虚传!听闻此物乃陛下亲设天工院所创,遇水凝结,坚如磐石,用于筑城、修路、建坝,无往不利。若我楚藩也能引入此物……”
朱华奎微微一笑,带着赞许,也带着一丝告诫:“引入自然是要引入的。但你要记住,此等国之重器,核心皆握于朝廷之手。陛下以此等利器修通天下道路,其意不言自明——加强中枢对西方之掌控。我辈宗亲,当顺应时势,切不可逆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