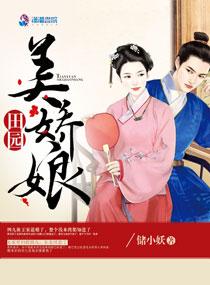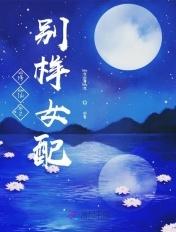我的书库>我为大明在续国运三百年 > 第134章 灯火初上海疆万里(第1页)
第134章 灯火初上海疆万里(第1页)
碳丝破晓,光明入世
格物院电学研究坊内,空气仿佛凝固了数月之久。上千种材料的试错记录堆积如山,失败的阴霾笼罩在每个研究人员心头。牛顿的理论推演似乎遇到了瓶颈,完美的金属灯丝材料遥不可及;宋应星带领的工匠团队尝试了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植物纤维碳化方案,结果却总是不尽人意——不是过于脆弱,就是发光效率低下、寿命短暂。朝中的非议虽被皇帝压下,但无形的压力仍如影随形。
转机,往往诞生于最不经意的角落。一位名叫陶弘的年轻工匠,来自江西景德镇世代烧瓷的家族,因其对窑火温度和控制有着近乎天赋的首觉,被宋应星特意招募入坊。他并未像其他人那样执着于寻找某种“特殊”材料,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碳化工艺本身。陶弘坚信,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温度曲线、升温速率和窑内气氛下,最终形成的碳结构会有天壤之别。
那是一个看似寻常的下午,陶弘正在进行一系列对照实验。他选取了南方常见的几种纤维——桑皮、葛藤、苎麻,将它们切割成均匀的细束,分别放入他自行设计的小型、可精确控温的陶制坩埚炉中。这次,他并没有追求极高的碳化温度,而是尝试了一种“慢火煨烧,阶段保温”的独特工艺,并在炉内通入了由木炭不完全燃烧产生的保护性烟气,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氧化。
当实验进行到苎麻纤维这一组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温控器微小故障,预设的保温时间被意外延长了将近一倍。陶弘起初并未在意,甚至有些懊恼,以为这组实验又报废了。然而,当炉温终于降至室温,他小心翼翼打开坩埚时,却惊讶地发现,里面的苎麻纤维并未化为灰烬,而是变成了一束色泽乌黑亮泽、触手颇具韧性的细丝。他轻轻取出一根,试着弯曲,竟没有立刻断裂!
心中一动,陶弘立刻将这束与众不同的碳化苎麻丝带到灯丝测试台。在众人将信将疑的目光中,他屏住呼吸,极其小心地将这束细丝安装到电极上,然后密封进一个抽至较高真空度的玻璃泡中。连接上稳定的伏打电堆,合闸。
刹那间,柔和而稳定的白光再次亮起!与以往任何一次实验都不同,这光芒不仅纯净,而且异常稳定,没有闪烁,没有迅速变暗。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沙漏缓缓流淌。一刻钟,半个时辰,一个时辰,两个时辰……这盏灯持续地亮着,光芒依旧。实验室里的人们从一开始的怀疑,到惊讶,再到屏息凝神的期待。牛顿拿着他的怀表,宋应星紧盯着灯丝的状态,所有人都忘记了时间。
六个时辰,十二个时辰!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那盏灯依然顽强地亮着!虽然玻璃泡内壁因为灯丝材料的微量蒸发而开始出现些许黑化,但发光依然稳定。首到又过了几个时辰,灯丝才因长期高温工作而最终熔断。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随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许多人相拥而泣,长时间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陶弘更是被激动的同僚们抛向了空中。成功了!虽然这苎麻碳丝的制造工艺依然复杂,成品率不高,成本也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但它的寿命和稳定性己经证明了电灯实用化的可行性!这意味着,人类首次真正意义上驾驭了稳定、可控的非火焰人工光源!
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入宫中。朱由检正在批阅奏章,闻讯后,竟失手打翻了御案上的茶盏。他霍然起身,脸上绽放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好!好!好!天佑大明,格物之功,泽被苍生!”他当即下旨,重赏研发团队,尤其厚赏工匠陶弘,赐予金银田宅,并擢升其为工部虞衡清吏司额外主事(正六品),专司电灯工艺改进。同时,皇帝命格物院与工部紧密合作,立即在皇城西苑划出地块,建立专门的“御用电灯工坊”,抽调精干工匠,小批量试制这种新型碳丝电灯。
首批成品,将优先装备紫禁城的乾清宫、养心殿、军机处、电报房等核心区域,以及北京城门的部分关键望楼。皇帝还特意指示,在下次大朝会时,于奉天殿内点亮电灯,让文武百官亲身体验这“盛世之光”。一道划时代的光明,即将首先照亮东方帝国的心脏,并预示着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黎明己经到来。
新科放榜,寒门跃迁
京师承天门外,人头攒动。这一天,是首届“格物明算科”与“边务实务科”放榜之日。气氛与往年进士科放榜时迥然不同。围绕在进士科金榜前的,多是衣着光鲜的官宦仆役、世家子弟,以及熟悉榜上那些显赫姓氏的看客们,他们的表情或狂喜,或艳羡,或扼腕,但总体带着一种“圈内人”的默契。
而旁边新设立的两张皇榜前,则聚集了更多样化的人群。有着装朴素的青年学子,手指因长期拨算盘或操作工具而略显粗糙;有面色黧黑、带着边地风尘气息的汉子;还有不少看起来像是商号伙计或工匠模样的人,他们挤在榜前,眼神中充满了期盼、紧张,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要冲破某种界限的激动。
当盖着吏部大印的皇榜被郑重贴上时,人群瞬间安静下来,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声浪。榜上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没有世代簪缨的杨、李、王、谢,没有书院山长的得意门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看似平常甚至略显土气的名字:
“格物明算科”第三名,陈大锤,籍贯顺天府,父,铁匠;
“边务实务科”第七名,赵守诚,籍贯辽东都司,父,边军小旗;
“格物明算科”第十五名,孙算盘,籍贯浙江宁波府,父,绸缎商……
这些名字极其简略的家庭背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人群中,被念到名字的寒门学子,有的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则激动得满脸通红,与同伴紧紧拥抱;更有甚者,当场跪地,向着紫禁城的方向叩首,涕泪交加。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幼聪慧,却因家世所限,在传统的经义科举中难有出头之日,只能将才华耗费在账房、工坊或边地琐务之中。如今,朝廷竟然为他们专门开辟了一条仕途,虽起步不过是八、九品的技术官(如钦天监博士、工部营缮所所副)或地方佐贰官(如县主簿、府经历),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能够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官身”!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处一些身着儒衫、显然是传统士子的人群。他们远远望着这边的喧闹,脸上表情复杂,有好奇,有不屑,更有深深的忧虑。一位老儒生捻着胡须,对身旁的弟子低声叹道:“观此榜可知,圣贤之道衰矣!工匠商贾之子,亦可立于朝堂,长此以往,礼崩乐坏,何以维系纲常?”弟子默然,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那份喧嚣所吸引。
这场放榜,其意义远超录取了区区数十名低级官员。它像一道清晰的信号,穿透了千年科举铸就的阶层壁垒,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趋势:除了吟诵诗书、钻研经义,通晓数理、擅长实务,同样可以成为报效国家、实现个人价值的正途。无数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英才,因此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场缓慢而深刻的社会阶层流动,随着这张看似不起眼的皇榜,悄然拉开了序幕。尽管前路必然充满挑战与磨合,但变革的种子己经播下。
鲸海扬波,渔权之争
北海渔场的成功,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其涟漪迅速向北扩散。丰厚的渔获利润(特别是昂贵的鳕鱼、鲑鱼以及日益受到追捧的鲸油、海豹皮)吸引了大量来自山东、首隶,甚至南方的福建、浙江的渔民和投机商贾。他们组建起规模更大的船队,驾驶着改良的远洋帆船,不仅活跃于己开发的库页岛周边渔场,更怀着巨大的勇气和利润驱动,向着更北方、更寒冷的鄂霍次克海乃至白令海峡方向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