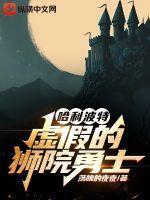我的书库>长夜君主 > 第八十九章 气运凝聚仙人指路二合一(第2页)
第八十九章 气运凝聚仙人指路二合一(第2页)
孩子们围着他,纷纷捡起树枝,在泥土上描摹那团火焰。
与此同时,大陆各地悄然兴起一种新习俗:每逢月圆之夜,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一盏素纸灯笼,不写名姓,不祭亡魂,只为纪念那段曾由一人肩扛光明的岁月。人们称之为“思灯节”。
没有人规定必须参与,可十年过去,九境之内,无一村落遗漏。
时间如水流逝,二十年光阴转瞬即过。
曾经的新一代孩童已长大成人,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做了医者,有的踏上讲学之路,走遍荒村野岭,只为告诉更多人:“你也可以发光。”
而苏璃,依然住在东荒山谷的茅屋中。她白发苍苍,身形佝偻,每日清晨仍会煮一壶茶,放在石桌上,对面空着的石凳仿佛永远等着某个人归来。
春天依旧带来蓝雪花,香气弥漫整个院子。她坐在藤椅里看书,书页泛黄,正是那本《长夜纪事》。村里孩子常来找她讲故事,她从不拒绝。
“奶奶,林小凡最后去哪儿了?”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仰头问。
苏璃合上书,目光投向远方山脊,那里晨雾正慢慢散去。
“他去了所有需要光的地方。”她说,“有时候是在母亲哄孩子入睡的歌声里,有时候是在父亲冒雨修屋顶的背影中,有时候……是你递给同桌半块馒头的那个瞬间。”
孩子似懂非懂,却又用力点头。
傍晚时分,一位旅人路过山谷,背着旧布囊,衣衫洗得发白。他在竹篱外停下脚步,望着院中老人的身影,久久未动。
苏璃忽然抬头,似有所感。
两人隔篱相望,旅人摘下斗笠,露出一张平凡却温和的脸。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身影渐渐隐入暮色。
苏璃没有追上去,也没有呼唤。她只是低头抚摸膝上的书,指尖抚过那行飘落的书签小字:
**“吾等皆凡人,故此道可久行。”**
当晚,她梦见了年轻时的林小凡,穿着粗布麻衣,坐在石凳上削木笔。刀锋轻推,木屑如雪。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梦中的他问。
“当然。”她答,“不靠神明,不倚圣贤,只信人心尚有微光。”
“那就够了。”他笑着抬头,眼中星辰闪烁,“这一世,我没白来。”
翌日清晨,苏璃安然离世。
她走得很安静,嘴角含笑,手中仍握着那枚玉佩。村民们将她葬在屋后山坡,墓碑无名,仅刻一行字:
>“她曾点亮第一盏灯。”
多年以后,南疆祖林重建为“守心书院”,不再供奉任何雕像或神器,唯有一面巨大的空白石墙立于主殿中央。墙上没有任何铭文,却总能在不同人心中映出不同的画面??有人看到母亲的脸,有人看见恩师的背影,有人仿佛听见挚友临别的话语。
承愿活到了九十岁,临终前召集所有弟子,只留下一句话:“我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真正的守心者,永远在路上。”
说罢,他闭目而逝。眉心一点金光缓缓升起,化作一只小小金羽飞鸟,振翅掠过书院上空,最终消失在天际。
自此之后,每隔百年,便会有人声称在极寒雪原、深海孤岛、火山腹地甚至废弃村庄中,见到一位徒步前行的旅人。他衣着朴素,背负布囊,囊中装着冰晶、铜钱、残卷与油灯。
他从不言语,只在夜深人静时,为熟睡的孤儿掖好被角,为熄灭的炉火添一根柴,为迷途的旅人指一条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