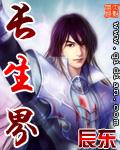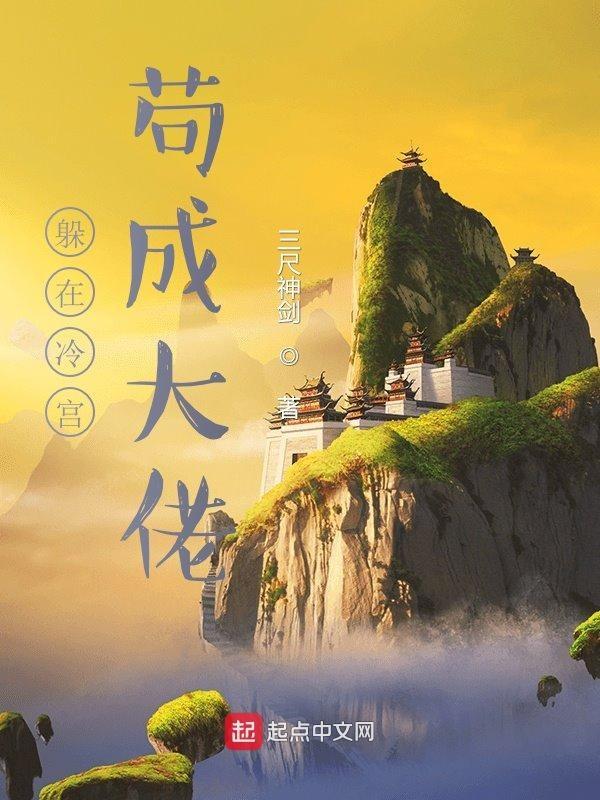我的书库>华娱,不放纵能叫影帝吗? > 第629章(第2页)
第629章(第2页)
她蹲下来,认真看着她的眼睛:“你能当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你一直敢做梦。”
当晚,她在日记本上写道:
>“今天我才明白,《风起陇西》的意义不止于银幕。它像一颗火种,落在荒原上,竟真的烧出了光。这些孩子不会一夜成名,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走出大山,但他们知道了??有人愿意为他们写故事,有人相信他们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
>这不是慈善,这是偿还。我还给这个行业的,不该只是票房和奖项,而是让更多普通人知道:艺术不是高墙内的奢侈品,它是照亮黑暗的灯。”
第三天清晨,她离开学校。临行前,孩子们送她一幅手绘的画:一个女人骑马立于城楼之上,身后是漫天烽火,前方是朝阳升起。画角歪歪扭扭写着:“我们的陈砚妈妈。”
她收下了,放进随身包最里层。
返程途中,手机接连震动。姜闻发来消息:【Netflix不死心,又提了新条件??加钱到1。8亿,但要求全球同步上线前三周屏蔽国内平台,做成‘海外特供版’。他们觉得国内审查会影响口碑传播。】
她冷笑一声,回:【告诉他们,我的电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它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想割裂它,等于否定了它存在的意义。不卖,一个子儿都不多谈。】
刚发完,赵小芸来电。
“宁姐,我在排练《雷雨》第四幕,四凤跪地那段……我还是找不到那种‘被命运碾过还挣扎着爬起来’的感觉。”她的声音带着疲惫,“导演说我太用力,可我不用力,就怕撑不住。”
时宁靠在车窗边,望着飞驰而过的青山绿水,轻声问:“你有没有试过,先让自己彻底崩溃一次?”
“啊?”
“真正的情感爆发,往往发生在你放弃抵抗之后。”她闭上眼,“去找个没人地方,把自己摔在地上哭一场,哭到喉咙哑了,眼泪干了,再站起来。那一刻的平静,才是四凤最后的尊严。”
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传来一声极轻的“嗯”。
“记住,”她补充,“你不是在演悲剧,你是在替所有被压抑的女人说话。她们不敢喊的,你要替她们喊出来。”
挂断电话,她打开邮箱,发现一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邀请函:《风起陇西》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影像代表作”之一,在巴黎总部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主题展映,并配套举办青年导演工作坊。
附件里还有一段视频??是她在玉门关埋下石碑的画面,已被剪辑成三分钟短片,配乐是中国古琴曲《广陵散》,字幕写着:“一部电影如何唤醒沉睡的历史”。
她怔住了。
原来有些东西,一旦诞生,就不再属于创作者。
一周后,北京。她受邀出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新时代文艺创作座谈会”。会场设在老电影制片厂旧址,墙上挂着黑白剧照,空气中弥漫着胶片时代的气息。
发言环节,轮到她时,全场安静。
她没有拿稿子,只说了一句话:“十年前,我接第一部戏时,制片人问我:‘你想红吗?’我说想。他说:‘那你得学会放纵??放纵情绪,放纵欲望,放纵自己成为话题。’可今天我想说,真正的放纵,是克制之后的选择。”
台下有人皱眉,也有掌声响起。
“我们总以为流量即真理,热搜即价值。可当一部电影能让山区孩子相信英雄存在,能让外国观众重新审视东方叙事,这才是行业该追求的奢侈。”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年轻导演:“别怕慢,别怕穷,别怕没人懂。只要你还愿意为一个角色熬三个通宵改剧本,为一场戏带着群演练到凌晨两点,为你坚信的真实对抗资本的压力??你就还没输。”
散会后,姜闻在门口等她,手里拎着两杯热美式。
“说得够狠啊,”他笑,“估计明天就有媒体标题:《时宁炮轰娱乐圈乱象》。”
“让他们写去。”她接过咖啡,“反正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他低声,“刚才有几个投资人在后台议论,说你现在‘太理想主义’,不适合商业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