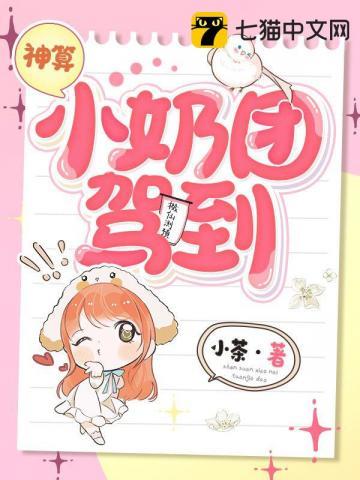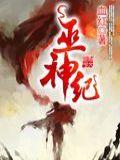我的书库>青葫剑仙 > 第两千五百三十二章 异香(第1页)
第两千五百三十二章 异香(第1页)
熊月儿在密林中急速穿行,四周古木越来越密,粗壮的藤蔓如巨蟒般缠绕在枝干之间。
忽然,前方荆棘丛生,无数布满尖刺的枝条如活物般蠕动起来,发出“沙沙”的声响。
这些枝条通体墨绿,尖刺上泛着幽光。。。
春雷滚滚,夜雨如丝。南荒的小院在电光中忽明忽暗,那棵槐树被风雨打得枝叶翻飞,却依旧挺立,仿佛守护着某种亘古不变的誓言。林晚晴没有动,只是将手中纸灯轻轻放在石桌上,任雨水打湿她的鬓角。她身旁的男人也未言语,只静静望着庭院里那一片被水洗过的青石板,仿佛在数着年轮刻下的痕迹。
良久,楚临开口:“你从未点过那盏‘归来’的灯。”
林晚晴笑了,笑得极轻,像风掠过水面。“我不敢。”她说,“怕点了,你就真的走了;不点,你还在我心里活着。”
楚临侧头看她,目光温柔如初雪融于掌心。“可我已经回来了。”他声音低缓,却不容置疑,“不是靠法术,不是借愿力,而是因为??你一直记得我。”
林晚晴指尖微颤。她知道眼前之人并非幻影,也不是愿海所化的残念。他是真实的,血肉与魂魄皆由千万人的记忆重塑而成,是无数人心中不肯熄灭的一缕执念凝结成形。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忘即新生”最彻底的否定。
“你知道吗?”她低声说,“自从你走后,每年清明,村里的孩子都会自发来咱们院子里栽花种树。他们说,这里是‘青葫剑仙’最初醒来的地方。有人甚至把你的故事编成了童谣,在溪边唱给流水听。”
楚临微微一怔。
“……他们还记得我?”
“岂止是记得。”林晚晴转过脸,眼中泛起水光,“江南有个书生,写了本《忆楚录》,里面记下了你从南荒归来、重燃十万心灯的事迹。他说你是‘以情为骨,以愿为脉’的真仙。这本书被官府列为禁书,烧了三次,可每一次都从民间重新传出来。西域那边更离奇,有商队说你在沙暴中引路,护送驼铃穿越死境;北疆老兵每逢祭日,都要朝南方敬酒三杯,说是敬‘那位穿青袍的将军’。”
楚临闭上眼,胸口起伏。这些名字他大多不知,这些人他从未见过,可他们的记忆,却成了支撑他归来的桥梁。
“所以……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喃喃道,“我是被所有人一起拉回来的。”
雷声渐远,雨势转小。院外传来??脚步声,几个孩童打着油纸伞跑来,怀里抱着新采的野花。领头的小女孩仰头看着屋檐下的两人,怯生生地问:“娘,这就是你说的青葫剑仙吗?”
林晚晴点头:“是他。”
小女孩走上前,把手中的白花放在门槛前。“爷爷说,他曾梦见一个穿青袍的人站在雪地里,问他冷不冷。后来爷爷病重时,最后一句话是‘谢谢你还记得我’。”她顿了顿,认真地说,“我也想谢谢你,让我做了个好梦。”
楚临弯腰,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这一瞬,天地仿佛静止。远处山林间,竟有无数萤火悄然升起,如同星河流转,汇聚而来。它们绕着小院盘旋,最终融入槐树根下那一方泥土之中。
他知道,那是散落人间的记忆之光,正悄然归位。
翌日清晨,阳光破云而出。楚临独自登上后山,来到当年埋下“真名印”的地方。玉符早已碎裂,但当他伸手触地时,整座山峦竟微微震颤。地下深处,九曜星辰的投影缓缓浮现,第八星炽烈如火,第九星虽仍黯淡,却不再熄灭,而是如呼吸般明灭交替,似在积蓄力量。
“原来如此。”他低语,“愿海未亡,只是沉睡。它需要新的锚点,新的信标……而这次,不能只靠我一个人的名字。”
他取出随身携带的一枚竹简,那是他在京都逆愿阵崩毁前,从废墟中抢出的残卷??《忆堂手札?第一册》。上面记载着每一位曾前来忆堂求学之人的姓名、籍贯与心愿。短短三年,已有十万三千余人留名于此。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不愿遗忘的情感:思念亡妻的老农、寻找兄长的孤女、渴望和平的退伍兵卒……
楚临盘膝而坐,将竹简置于膝上,双手结印,口中默诵《愿海诀》中最古老的篇章??《众生愿》。
随着咒文响起,竹简上的墨迹竟开始发光,一个个名字浮空而起,化作微弱却坚定的光点,升入苍穹。它们并未汇入九曜星辰,而是洒向四方,落入风中,随气流飘散至大江南北。
这是全新的开始。
从此以后,忆堂不再依赖某一位英雄的存在与否,而是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象征。只要还有人愿意写下所爱之人的名字,愿意为逝者点灯祈福,忆堂的精神就不会断绝。
七日后,第一批回应到来。
江南某镇,一名老妇人在祠堂前焚香祷告,忽然泪流满面:“我想起来了……十年前,我儿子战死沙场,是我亲手烧了他的遗物。可昨夜他托梦给我,说有人替他在战场上收尸,并用一方素布裹身带回故里。那人穿着青袍,剑上有朵白花……他还说,‘母亲不必自责,儿已安息’。”
同日,北疆边关守将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枚锈迹斑斑的铁牌,正是十年前失踪斥候的军籍令。信上只有一行字:“他叫李青山,家住雁门关外柳河村。他没有逃,也没有叛,他死在狼群口中,手里还攥着敌军的地图。”
又三日,西域沙漠边缘出现一座无名石碑,碑文如下:
>“此处埋骨者,乃商旅张远舟。丙戌年七月十四,遇沙暴失联。幸得青葫剑仙相助,引其魂归故里。其妻王氏,每夜焚香,终闻其声。谨立此碑,以证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