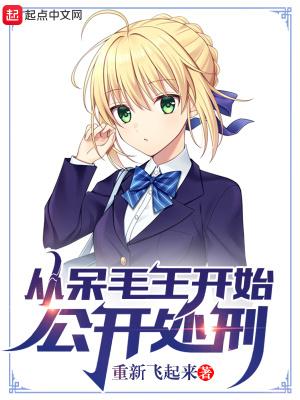我的书库>乱战异世之召唤群雄 > 第1374章千里不改忠章志十万大军归汉手中(第1页)
第1374章千里不改忠章志十万大军归汉手中(第1页)
张宾毫不留情的将他们这十余万镇南军的困境揭露了出来。
此言一出,帐内一片死寂,只有马千里粗重的喘息声和火盆的噼啪声。
每一个将领的脸色都更加难看,张宾的话就像毒针一样,精准地扎破了他们最后。。。
夜雨初歇,长安城外的山道上浮起一层薄雾。赵云龙坐在“铭记园”的水镜前,笛声已止,余音却仍在林间游走。孩子们早已散去,唯有那支旧竹笛静静横在膝头,仿佛也沉入了回忆。
他闭目良久,忽觉指尖微动??是林氏的手轻轻覆了上来。
“你又在想过去的事了。”她轻声道,声音如春溪流石,温润而清晰。
赵云龙睁开眼,望着她眉宇间的宁静,竟一时说不出话。五年光阴,未曾磨淡她的容颜,反倒让那份沉静愈发深邃。她不再是那个甘愿沉眠于绝望之中的祭官后裔,而是成了千万人记忆的守护者。《情录》已编至第三十六卷,每一章都是一段被遗忘的情感重见天日。
“我在想……”他缓缓开口,“我们真的赢了吗?”
林氏微微一怔。
“归墟七核,六门现迹,唯‘绝核’因我之情而退。可其余六门呢?贪、惧、疑、惰、妒、妄??它们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模样,在人心深处悄然蛰伏。”
林氏蹲下身,指尖轻点水面。墨迹未干的名字正随波轻颤,“阿勇”二字忽明忽暗,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
“你说过,战场不在地下,而在人间。”她抬头看他,“那胜利也不该以‘彻底消灭’来衡量。若有一人因听了一个名字而停下恶念,若有一瞬因一段记忆而选择善良??这便是胜。”
赵云龙沉默片刻,忽然笑了:“你总能让我看清自己看不见的东西。”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守心司密探疾步而来,衣角沾泥,显然是连夜赶路。他单膝跪地,呈上一封火漆封缄的信函。
“敦煌急报!星塔第七次鸣响,三短一长??‘**蜕门再启**’。”
赵云龙接过信,拆开只扫一眼,脸色骤变。
“不是六门之一……这次是‘**心冢本源**’。”
林氏倒吸一口冷气:“不可能!心冢乃七核交汇之地,传说唯有七钥齐聚、七门同开方可唤醒。如今仅‘绝门’曾现,其余皆无异象,怎会……”
“有人在强行召唤。”赵云龙站起身,目光投向西北方向,“而且,那人……用的是‘名契之力’。”
所谓“名契”,正是近年来兴起的记忆契约制度??凡见证他人牺牲者,须将其名记入家谱或碑文,以此延续其存在。本为对抗遗忘而设,如今竟被人逆用为开启深渊的钥匙。
“是谁?”林氏问。
“信中提到一个名字??**秦无咎**。”
“什么?!”赵云龙猛地转身,“不可能!他早在二十年前就死在羽渊潭洪水中!”
“可敦煌残卷最新一页写着:‘昔年溺亡者,实为替身。真身藏于江南书院之下,借百家诵名之力建‘伪我’,积聚信念,欲以万民之忆为薪,点燃心冢之火。’”
赵云龙双拳紧握,指节发白。
秦无咎,曾是江南书院最负盛名的儒生,也是最早提出“名学运动”的先驱。他曾高呼:“死者若无人记,则等于未活。”也曾奔走四方,为无名者立传。谁能想到,这位被誉为“记忆之父”的人,竟是归墟最初的缔造者之一?
“他不是要毁灭世界。”林氏低声说,“他是想重建它??按他的方式。”
“他认为人类不配拥有自由意志。”赵云龙冷笑,“所以他要用‘集体记忆’铸造一座永恒牢笼,所有人活着只为记住‘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没有怀疑,没有背叛,也没有痛苦……只有整齐划一的铭记。”
“那不是记忆。”林氏摇头,“那是洗脑。”
翌日清晨,七门监察司紧急集议。秦昭主持会议,面色凝重。
“根据敦煌传回的情报,秦无咎已在太湖底构筑‘忆宫’,以三千名自愿献忆的‘铭奴’为基,日夜吟诵特定名字,形成共振场。这些名字并非真实英雄,而是他虚构的理想人格??‘仁君张衡’‘义士李靖’‘忠臣王安’……每一个都是完美无瑕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