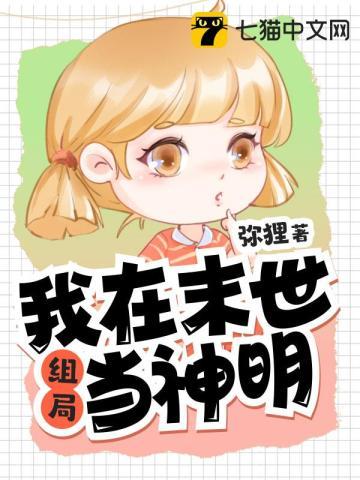我的书库>家族修仙:开局成为镇族法器 >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章 雷女(第2页)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章 雷女(第2页)
>“烧错了方向?不。
>是时候重新点燃了。”
原来,当年追随老妪的逃亡者并未消散。他们在雪原深处建立“反忆堂”,专收那些因过度思考而濒临崩溃之人。不同于思想安宁局的“转移”,他们提倡“共担”??一群人围坐篝火,轮流讲述自己的困惑,不求解决,只求被听见。
一位年轻修士曾在终律殿修行三十余年,坚信“万法归一”。后来他接入黑水晶,成为首批休眠者。苏醒后,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现实,几欲自尽。直到在反忆堂听到一个牧童哭诉:“我怕羊丢了,也怕我自己丢了。”那一刻,他突然泪流满面,跪地痛哭:“原来我也一直在怕。”
如今,反忆堂已有三百余座分舍,遍布九州。它们不立碑,不传教,只在每个夜晚点燃一盏油灯,门扉敞开,静候迷途者推门而入。
而在南荒启明院,问己碑的变化愈加显著。它不再被动显现历史遗问,而是开始主动“回应”。每当有人诚心叩问,镜面便会泛起涟漪,映出的不再是提问者的脸,而是另一个与此问题相关的陌生人??可能是百里之外的樵夫,也可能是万里之遥的渔女,甚至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
人们渐渐明白:每一个问题,都在无形中连接着他人。你问“如何面对失去”,或许正有另一人在同一时刻问“如何学会告别”。你们从未相识,却因疑问共振,如同两颗星在黑暗中彼此感应。
于是,启明院外兴起一种新习俗:人们携笔墨而来,在碑前写下问题,然后将其折成纸鸢放飞。据说,若风向恰好,纸鸢会跨越山海,落入某个同样困惑的心灵手中。
这一年春末,幽冥谷底的残碑忽然震动。藤蔓退去,泥土剥落,整块石碑缓缓升起,悬浮半空。随后,碑体裂开一道缝隙,从中飞出一只通体碧绿的蝴蝶,翅翼上隐约可见古篆:“行”。
蝴蝶振翅而去,一路北上,途经西漠、东海、南荒、北境,凡其所至,疑塾灯火皆自动明亮三分。最后,它停在冰渊共念体上方,轻轻扇动翅膀。
霎时间,那团雾状存在剧烈震荡,发出一声悠长鸣叫,竟分裂为千百团小型意识体,如萤火四散飞离,融入人间烟火。
观测者记录下这一刻,命名为“**散念之日**”。
此后三年,九州再无统一的思想控制机构。黑水晶残片被熔铸成铃铛,挂于各村学堂檐角;安宁局遗址改建为“疑园”,园中遍植会发光的问心草,夜间漫步其间,常能听见草叶低语:“你还好吗?”“你在想什么?”
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少年的成长环境已然不同。他们不再被要求“坚定信念”,而是被鼓励“保持好奇”。修仙之道也不再局限于炼丹御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修习“问心术”??一门专注于倾听、表达与共情的技艺。
某日,一名少女在山中采药时迷路,饥寒交迫之际,遇见一位独居老者。老者见她手腕上有守夜盟约印记,便问:“你也信‘提问即修行’?”
少女点头:“老师说,每一次发问,都是灵魂的一次呼吸。”
老者沉默良久,忽而笑道:“那你可知,最早提出这句话的人是谁?”
少女摇头。
老者指向山谷深处:“他曾是个瞎子,拄着焦木拐杖,走遍天下。有人说他是神,有人说他是疯子。可我知道,他只是一个太在乎‘为什么’的人。”
少女离开后,老者取出一枚陈旧铜铃,轻轻一摇。铃声清越,传入密林深处。片刻后,林间光影微动,一道身影浮现??仍是明烛,只是须发已斑白,眉宇间尽是岁月沉淀的宁静。
“她问对了。”他说。
老者微笑:“可你已十年未现于世人眼前,为何今日肯露面?”
明烛望向南方:“因为新的风暴正在酝酿。共念体虽散,但‘终解之影’并未真正消亡。它潜伏在某些人心中,化作另一种形态??不是强迫人接受答案,而是让人彻底放弃提问。”
他取出一枚新的心泪,递给老者:“帮我交给下一个愿意听声音的人。”
老者郑重接过,低声道:“你会去哪儿?”
明烛转身步入林中,身影渐淡,唯余声音飘散风里:
“去找那些还没开口的孩子。去告诉他们,哭也没关系,怕也没关系,只要心里还藏着一个问题,你就还没有输。”
多年以后,当那位少女也成为导师,她在课堂上对学生说:“不要怕问傻问题。因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错误的答案,而是从此不再提问的人。”
窗外,春风正好,吹动檐下铜铃。叮咚一声,似有回应。
而在极北孤庙,那口旧箱再次被打开。兽皮简牍虽已焚毁,但箱底暗格中,竟藏着一张泛黄地图,标注着九处隐秘地点,分别对应“问火”“心泪”“承思”“散念”“惧册”“碑移”“火返”“终解”“启明”。
地图背面,一行小字清晰可见:
>“旅程未完,
>问题永续。
>下一站,由你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