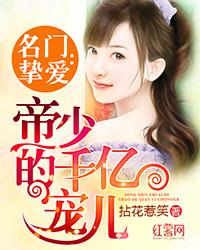我的书库>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288 正反手(第3页)
288 正反手(第3页)
林远看着地图上那个小小的红点,位于横断山脉深处,距最近的公路还有八十公里土路。
“你说的那个山村?”他问。
“是。”她说,“全村九年间因泥石流、车祸、疾病失去十四位亲人。其中七个是孩子父母。学校老师反映,学生们几乎从不提及逝者名字,害怕‘说了就会忘记’。”
林远沉默片刻,调转方向。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他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们花了几十年让AI学会理解人类情绪,可现实里,我们却教孩子压抑悲伤。好像哭一场,就是软弱;提一句死者,就是打扰活着的人。”
“所以你需要去那里。”她说,“不是为了推广系统,而是让他们知道??想念,是一种力量。”
三天后,林远抵达云岭村。
这里没有信号塔,没有电网,家家户户靠太阳能板维持照明。村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物,眼神沉静如古井。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十四个名字,最小的只有八岁,最大的不过四十二。
他带来了一套便携式共梦终端,由太阳能充电,支持离线语音采集与本地回放。他还带了三百份空白录音卡带??这个时代早已淘汰的东西,却是最适合这里的媒介:无需网络,不怕黑客,老人孩子都能操作。
第一天,没人理他。
第二天,有个老太太悄悄问他:“真能让死去的儿子跟我说话?”
林远摇头:“不能。但我可以让您说的话,传到他曾经最爱坐的那棵核桃树下。”
老人哭了。
当晚,她录下第一段语音:“石头啊,娘今天腌了你爱吃的酸萝卜,要是你在,肯定偷吃……你走后,我每天烧饭都多煮一碗,怕你回来饿着……”
第三天清晨,全村人都听见了。
那棵老核桃树上绑着一台小型喇叭,正播放着这段话。声音不大,却穿透晨雾,落在每个人的窗前。
一个男孩蹲在树下听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抱着树干嚎啕大哭。
从那天起,人们开始排队录音。
有丈夫对亡妻说“今年苞谷收成好,够你酿酒了”;有女儿对自杀的母亲说“我不怪你,我只是想再抱你一次”;有个七岁女孩对着麦克风唱完《小星星》,然后小声问:“妈妈,你在天上能看到我吗?”
林远把每一段都存进卡带,分发给家属。他还教会几个年轻人搭建简易广播网,让这些声音能在清明、忌日、生日时自动播放。
第七天,村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对话节”。所有人聚集在祠堂前,轮流播放亲人的语音。没有哀乐,没有跪拜,只有一个个平凡至极却又重若千钧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林远站在人群外,听着听着,忽然发现自己的记忆正在恢复。
不是全部,而是一点一点,像春雪融化。
他想起了苏苗第一次骑自行车摔破膝盖,趴在他肩上抽泣;想起了她躲在被窝里看漫画书被发现时调皮的笑容;想起了她睡前总要听三个故事才肯闭眼……
原来,当更多人开始说出“我想你”,那些曾被牺牲的记忆,也会被温柔归还。
一个月后,林远离开云岭村。
临行前,村长递给他一卷手工缝制的布带,上面绣着十四个名字。
“以后不管去哪儿,带着它。”老人说,“这些人,也是你的家人。”
他又上路了。
青海湖畔,他帮一对老年夫妇重建了亡子的语音模型,让他们能在风雪夜里听见“爸,妈,我吃饱了”;在川西牧场,他教会牧民用牛铃编码思念,通过共振传递哀悼;在贵州侗寨,他协助村民将祖辈口述史诗录入系统,让百年记忆不再依赖口耳相传。
每到一处,他就留下一套设备、一批卡带、一群志愿者。
而remember-me。net的影响力持续扩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数字人文遗产保护典范”,尽管中国政府仍将其列为非法平台,却默许偏远地区使用离线版本。欧美多国发起“记忆权”立法讨论,主张“个体拥有保存与传递情感数据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她的声音开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