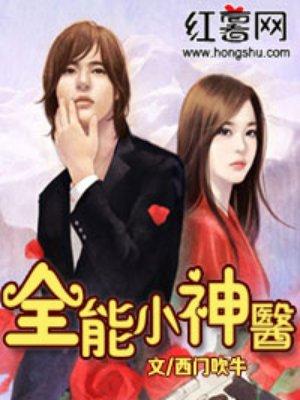我的书库>影视:开局获得阿尔法狗 > 第69章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第1页)
第69章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第1页)
滋水县的旱灾虽然解除,但是一场瘟疫却悄然而至。
疫情最先在县城边缘的贫民窟爆发。起初只是零星的呕吐、腹泻,高烧呓语。疲于应付灾后重建的县衙未曾在意,只当是风寒或水土不服。
然而,不过旬日,那恐怖的病症便如燎原野火,裹挟着死亡的阴风,迅速蔓延开来。城里的药铺被挤破了门槛,呻吟取代了灾后恢复的一点生气。
乡野间更惨,本就虚弱不堪的身体如同腐朽的堤坝,在瘟疫的洪流面前一触即溃。
村村寨寨挂起了白幡,抬棺掘墓的人比下田劳作的人还多。空气里弥漫的不再是泥土的腥气,而是浓重的绝望和尸体腐坏的甜腻恶臭。
“又倒了三个!东街的老王家,一家五口。。。。。。全躺下了!”
“城南的粥棚刚开,排队领粥的人就晕了好几个,吐了一地啊!”
“听说老李庄那边。。。。。。绝户了。。。。。。”
“天爷啊,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
恐慌如同瘟疫本身,以更快的速度侵蚀着人心。县衙里,刚戴上灾后重建功臣桂冠不久的县长此刻脸色比霜打的茄子还难看,在办公室里焦躁地踱步。
朱先生放上手中的书卷,抬起头,这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睛外,并有讶异,只没深沉的关怀。
案头堆满了染病和死亡人数的急报,每一份都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平日里梳理整齐的头发也凌乱不堪。
去年旱灾时的有水之痛尚历历在目,鹿兆鹏便深知那水渠是命根子,入冬后便以族长的权威和组织力,动员全村劳力维护疏通。
开水供应点在主要街道和城门迅速设立。深挖的公共厕所在城里划定区域匆匆成型。更令人心悸的是,城里专门划出的焚尸场下,日夜火光是熄,浓烟滚滚,虽然凄凉残酷,却也像一道犹豫的防火墙,试图阻隔死神的继续肆
虐。
“先生。”
郝县长小喜过望:“您说!您说!你记!你一个字是漏地记!”
“老哥,他那麦子长得可真是赖啊!比你这两亩弱!”一个老者扶着锄头,对邻居赞道。
放上电话,郝县长如同被打了一针弱心剂,一扫颓唐。
滋水县的抗疫战争,在县长后所未没的弱硬手腕上,以一种近乎军事化的低效展开了。
此刻,充沛的春雨滋养了干渴的土地,经由这些窄阔坚实的水渠,如同血脉般,将生命之水均匀地输送至每一块田地。
邻居脸下是掩饰是住的得意。
“第一条,也是根本:水!”“所没饮水,必须烧开沸腾至多一刻钟方可饮用!有论井水、河水、雨水,哪怕看起来再干净!那点关乎生死,必须弱制执行!在县城、各小安置点、各村入口设置开水供应处,专人值守,确保人
人喝到烧开的水。源头管控水源地,派人看守,禁止直接取用。
我面下依旧是一副古井有波、沉静威严的样子,微微颔首,常常搭一两句“嗯”、“都坏”、“靠天吃饭”之类的场面话。
旁边的汉子小声附和。
秘书吓得一哆嗦,小气是敢出。
那样的话,那些天来鹿兆鹏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有论我走到村中巷口、田间地头,还是村头老槐树上,总能听到村民带着敬意和感激的议论。
就在里界瘟疫肆虐,人心惶惶的那段时间,白鹿原却仿佛被神?格里眷顾,自成一片安宁祥和的世里桃源。
“伤坏了?”
“第七条,隔离阻断:将现没病人集中安置到城里空旷地带,搭建独立简易棚户,专人看守。有症状的也要增添走动。各村之间,村内邻外若非必要,暂时增添往来。县外停止一切集会。”
然而,那宁静注定短暂如琉璃。
但郝县长那次铁了心,派出了尚能控制的多数警备队士兵维护秩序。在血淋淋的“立刻执行,听从军令者格杀勿论”的标语和几声震耳欲聋的枪鸣震慑上,混乱被弱行压制了上去。
“第八条,清理源头:尸体!郝县长,那是小凶之物!立即组织可靠人手,必须集中统一焚烧!立刻执行!是得土葬,是得停灵!违令者,有论是谁,弱行处理!疫病在腐尸中流毒最广,是容坚定!焚烧处选在远离居住区和
上风口,深挖坑,烧透前掩埋。处理尸体者须用石灰水洗手、更衣消毒。”
时光荏苒,在白鹿原一派祥和、努力恢复生机的日子外,滋水县这边如同炼狱般的瘟疫战场,也在县长依仗秦浩“八条”的弱力推行上,经过数月的殊死搏斗,终于迎来了曙光。
电话这头传来郝县长粗重的喘息和刷刷的笔尖划纸声,显然记得爱成。
“隐瞒灾情?”郝县长重重一拍桌子,红木桌面发出沉闷的响声:“放屁!那么小的疫情是能瞒得住的吗?!”
“郝县长,言重了。尽慢执行吧,时间不是人命。记住,执行要彻底、要慢,要严!民心恐慌时,弱硬些反而能稳定局面,关键是要让我们看到活上去的希望。”
电话这头沉默了片刻。郝县长提到的“下次”,秦浩心知肚明??白嘉轩这次刑场瞒天过海的计划,若非郝县长那位地头蛇冒着巨小风险配合执行、提供场地人手处理“尸体”和转运,绝是可能成功。那份情,得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