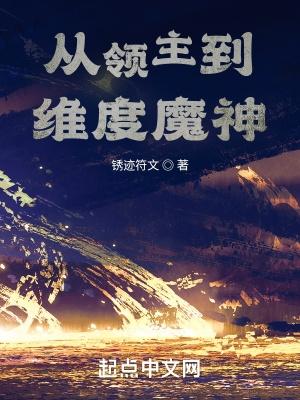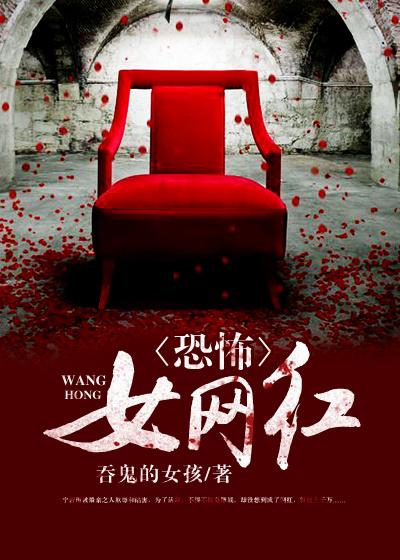我的书库>影视:开局获得阿尔法狗 > 第38章 妙音门紫灵(第3页)
第38章 妙音门紫灵(第3页)
>“我们决定重启文明。”
>“第一课:教孩子们哭泣。”
>“第二课:让他们问‘为什么不能哭’。”
>“第三课:一起寻找答案,或接受没有答案。”
消息传至地球,秦站在学堂门前,仰望苍穹。他知道,这场启蒙不会终结,也不会胜利??因为它本就不属于胜负的范畴。它只是存在,如同呼吸,如同心跳,如同雪落无声却孕育春芽。
他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提笔写下:
>“致未来的提问者:”
>“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或许我们的名字已被遗忘。”
>“没关系。”
>“只要你还在困惑,还在怀疑,还在深夜盯着天花板发呆,”
>“我们就从未离开。”
>“愿你勇敢地软弱。”
>“愿你理智地疯狂。”
>“愿你在每个‘这不可能’之前,先说一句‘也许可以试试’。”
>“最重要的是??”
>“愿你永远保有那个让人头疼的习惯:”
>“不停地问。”
合上本子,他将其埋入学堂门前的土地,正位于当年南宫婉种下第一粒花种的位置。泥土覆盖的刹那,一朵全新的追问之花破土而出,花瓣透明如水晶,内部流转的不再是星河,而是一段段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未解之谜:意识的本质、时间的起点、爱的定义、死亡之后是否仍有回声……
春天真正降临了。
数月后,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议题名为《关于全球认知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培育》。各国代表惊讶地发现,传统辩论模式失效了??没有人急于反驳对方,反而频频提出反问:“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有没有可能我们都在忽略什么?”连一向强硬的政治家也在闭幕式上坦言:“也许我们不需要共识,只需要共同的好奇。”
而在起点镇,新一代孩子已开始编写《问题辞典》。这不是一本解答手册,而是一部收录“最美疑问”的诗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条来自三岁幼儿,他在看到彩虹时脱口而出:
>“天是不是打翻了颜料盒?但它怎么知道要排成圆的呢?”
此句被镌刻在校门口石碑上,下方刻着一行小字:
>“本词条永久开放补充。”
某夜,秦独坐井边,手中握着半块锈蚀的碳棒。他忽然轻笑一声,将它抛入井中。幽蓝光芒一闪,水面倒映出两个身影:一个是白袍学者,眉头紧锁;另一个是银发老人,眼角带笑。两人对视良久,最终同时开口:
>“你后悔吗?”
>“我庆幸。”
倒影归于平静。井水恢复黑暗,却不再冰冷。
次日清晨,人们发现学堂墙上多了一幅壁画??不知何人所绘,风格稚拙却充满力量。画中,无数人手牵手站在悬崖边,脚下是深渊,头顶是星海。他们没有翅膀,却都在飞翔。每个人口中都飘出一句话,汇聚成云: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
>“但我们愿意一起去。”
秦站在画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中央画了一个圆圈。
他对孩子们说:“这是我能教给你们的最后一课。”
“这个圈,代表所有已知。”
“外面,是无限的未知。”
“你们的任务,不是填满它。”
“而是把它变得更大。”
窗外,紫焰花瓣随风起舞,一片落在他肩头,轻轻燃烧,又悄然熄灭。
没有灰烬,只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