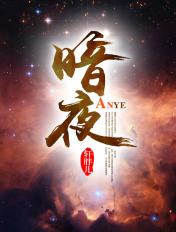我的书库>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44章 请仙子将苍长老留给我灵域(第2页)
第1544章 请仙子将苍长老留给我灵域(第2页)
阿萝怔住,随即眼眶微红。
“可总有人不甘心。”她低声道,“今早接到消息,西北某研究所试图提取归愿碑残余能量,声称要‘开发情感共鸣技术’。还有媒体在炒作‘守碑人真实身份’,甚至有人开始编造你和她的爱情故事……他们又要把她变成话题,变成商品,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消费。”
明川握紧了笔。
他知道,人性中最难克服的,不是仇恨,而是遗忘后的轻佻。当伤痛成为过去,人们总会急于翻篇,甚至用娱乐化的方式消解沉重。纪录片拍成偶像剧,纪念馆开起主题咖啡馆,连忆璃花都被注册成香水商标……这一切,都在无声地背叛着最初的誓言。
当晚,他写下一封公开信,通过“记得计划”官网发布:
>“我不认识沈昭宁。
>至少,在现实中从未见过。
>我所做的,不过是回应了一场跨越三百年的呼唤。
>她留给世界的,不是奇迹,不是神迹,而是一个选择:
>当你面对不公时,能否依然相信善良?
>当你承受苦难时,能否拒绝以恶报恶?
>她不是救世主,她是榜样。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下一个她。
>请不要再追问她的私生活,不要再幻想她的重生。
>她不需要雕像,不需要祭拜,更不需要被神话。
>她只需要??
>有人继续讲真话,
>有人愿意扶起摔倒的孩子,
>有人在黑暗中仍肯点亮一盏灯。
>这就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一夜之间,这封信被转发千万次。
热搜榜首悄然换上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好事#的话题。有人晒出自己匿名资助贫困学生的凭证,有人分享安慰陌生人的经历,还有老师上传课堂录像:学生们围坐一圈,轮流讲述“我做过最温柔的一件事”。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所有涉及归愿碑的研究项目,并发布严令:任何商业化使用“沈昭宁”及相关符号的行为,均属违法。首都非遗馆特别增设展区,展出的不是碑体本身,而是三百年前普通百姓的日记、信件与遗物??那些曾被历史忽略的微光。
春天渐渐深了。
医蛊堂门前的小路铺满了落花,忆璃花瓣随风飘舞,像一场永不停歇的蓝色雪。明川每天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带他们照料花草,讲述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关于勇敢,关于宽恕,关于在绝望中仍选择点亮灯火的人。
有一天,一个七岁女孩跑来找他,手里攥着半块烧焦的木牌。
“我在老屋阁楼找到的,”她怯生生地说,“上面有个名字,你看得懂吗?”
明川接过一看,心头猛地一颤。
那是一块祠堂残牌,边缘碳化严重,中间依稀可见三个字:**姜璃**。
年代久远,显然来自三百年前的昭宁祠遗址。
他立刻联系苏晚晴。经鉴定,这是当年焚毁祠堂时唯一未完全烧尽的信物,极可能承载原始记忆烙印。若能激活,或许能还原更多被湮灭的历史片段。
但他们不敢贸然行动。
上次开启归愿碑,几乎引发全国范围的精神震荡。这一次,必须万无一失。
经过七日筹备,他们在医蛊堂密室布下七重结界,由阿萝主持忆引仪式,苏晚晴监控脑波数据,明川作为唯一接入者,准备进入记忆回溯通道。
骨笛响起,音波如丝线牵引意识下沉。
画面浮现??
一座繁华古城,市井喧嚣。沈昭宁并非出身名门,而是民间医师之女,自幼聪慧,通晓药理与律法。她办义学、救疫病、为冤狱者奔走,声望日隆。然而正因如此,触动权贵利益。一场阴谋悄然展开:伪造她勾结外敌的证据,煽动民众恐惧,将她定为“祸国妖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