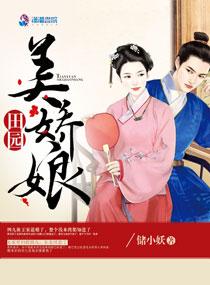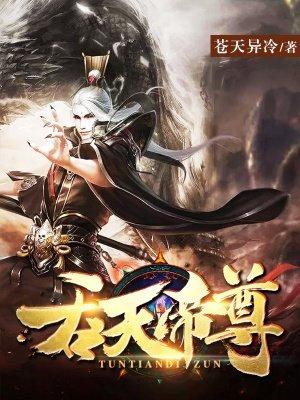我的书库>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46章 我们是盟友(第1页)
第1546章 我们是盟友(第1页)
月光如水,洒在青石板小径上,将两人的影子拉得细长。
金曼身上那件紫色纱衣在夜风中轻轻摆动,更添几分朦胧与神秘。
金曼侧头看向明川,妩媚的眉眼在月色下显得有些迷离,随即又化开一抹浅笑,带着几分自嘲,也带着几分坦荡。
“你猜得不错。”她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些,“我与圣域,确实有解不开的仇怨。当年在圣域……若非侥幸,世上早已没有金曼此人。逃到这灵域,栖身于青城御法宗,也不过是权宜之计,苟延残喘。。。。。。
暴雨过后,高原的清晨格外清冽。天边泛起鱼肚白,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如金线般洒落戈壁,照在那座已成废墟的研究基地上。钢筋扭曲,玻璃碎裂,空气中还残留着电磁灼烧后的焦味。远处几只野鹰盘旋而下,在残垣断壁间寻找食物,仿佛这片土地从未有过人类的痕迹。
明川站在山脊之上,背对着医蛊堂的方向,手中握着一只断裂的小提琴弦。这是他从基地里唯一带走的东西??来自那个被遗忘的测试室角落。那里曾堆满“记忆样本”,每一件都标注着编号与情绪类型:悲伤Ⅲ型、愤怒Ⅴ型、悔恨Ⅱ型……而那把小提琴,属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幸存者家属,他在视频留言中说:“她生前最爱拉这首曲子,可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风拂过耳畔,带着一丝凉意。明川将琴弦轻轻放入怀中,转身下山。
回到医蛊堂时,孩子们正围着阿萝学认字。苏晚晴坐在廊下翻阅一份加密档案,是昨夜刚从国际刑警数据库中调出的情报:林衍虽被捕,但其背后资助方仍未浮出水面。资金流向经过七层离岸账户,最终指向一个名为“新纪元共识会”的神秘组织。该组织宣称“唯有通过集体创伤唤醒民族觉醒”,在全球多地秘密支持极端主义思潮。
“他们不会罢休。”苏晚晴合上平板,声音低沉,“林衍只是棋子,真正想点燃仇恨火种的人,还在暗处。”
明川点头,在纸上写道:“所以我们要建一座桥,不是墙。”
阿萝接过纸条,轻声念出来,眉心微动。“你是说……让那些曾经对立的家庭坐在一起对话?”
他又写:“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为了让‘人’重新看见‘人’。”
这提议并不新鲜,早在上世纪就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尝试。但在信息碎片化、情绪极化的今天,一句真心话往往敌不过一段剪辑视频。仇恨网站虽被查封,可类似内容仍在地下论坛流转,换了个名字,换了种包装,却依旧煽动人心。
当天下午,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医蛊堂门口。
没有署名,只有一页泛黄的手稿,字迹颤抖却坚定:
>“我是当年签署逮捕令的三人之一。
>其余两人已死,一个自杀,一个病逝。
>我活了下来,不是因为无愧,而是因为我躲得够深。
>沈昭宁临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我亲自记录的。
>她说:‘请告诉未来的人,我不是符号,我是女人,我也怕疼。’
>这句话被删了。
>如今我患癌晚期,只剩三个月。
>若你们愿意听一个罪人的忏悔,我在南岭疗养院等你们。”
屋内一片寂静。
阿萝攥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这是真的吗?”
苏晚晴迅速核查地址与笔迹比对,两小时后确认:此人确为原司法系统高官陈砚之,二十年前因政治清洗运动掌握实权,后悄然隐退,外界皆以为他早已去世。
“他若真有悔意,为何现在才开口?”苏晚晴质疑。
明川沉默良久,提笔写下:“也许,直到此刻,他才敢面对自己。”
三天后,三人启程前往南岭。
山路蜿蜒,雾气弥漫。疗养院藏于竹林深处,白墙灰瓦,静谧得近乎压抑。陈砚之躺在轮椅上等他们,瘦骨嶙峋,双目浑浊,唯有眼神深处藏着一丝未熄的光。
见面时,谁都没有说话。
良久,老人缓缓开口:“我知道你不恨我,因为你从不恨任何人。可我恨我自己,三十年了,每晚都在梦里听见她的脚步声走向刑场,而我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签了那份文件。”
他颤巍巍地从枕头下取出一本日记,封皮磨损,边角卷起。“这是我每天写的。从她死后第二天开始,一天不落。我不求宽恕,只希望……有人能把这些读完,然后决定要不要烧掉它。”
明川接过日记,翻开第一页:
>**1994年3月18日晴**
>今日执行死刑。沈昭宁,女,32岁,无党派,作家。罪名:传播颠覆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