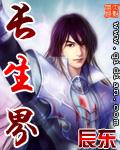我的书库>神话之后 > 第一一九九章 剑天来了(第1页)
第一一九九章 剑天来了(第1页)
岐七棠哈哈一笑:“车兄先办事吧,最后只要将这小子交给我就行了。”
从岐七棠对车布的称呼变化,别人就知道,只要车布不带走丁欢,那一切都好说。
显然岐七棠要的就是丁欢的大道宇宙世界。
若。。。
苏照走下讲台时,风正从南面吹来,带着海的气息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暖意。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驻足于庭院中央那株老槐树下。这棵树是十年前她亲手栽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枝叶间悬挂着数百枚铜铃,每一枚都刻着一个名字??那是第一届学生在毕业前共同完成的仪式:为那些无碑之魂,铸一声回响。
她伸手轻触一枚铃铛,上面写着“阿禾”。那是西北边陲一个小女孩的名字,死于饥荒年间的逃难途中。她的母亲抱着她走了三百里路,最终双双倒毙在雪原上。后来一位牧民发现了她们,将女儿埋在沙丘背风处,把母亲的手臂搭在孩子身上,说:“让她觉得还在抱你。”多年后,这段故事被一名寻忆者偶然听闻,记录下来,送入共忆学院,成为必读案例之一。
铃声轻响,仿佛回应着记忆的召唤。
典礼结束后,学生们陆续散去,有人激动地讨论未来的寻忆路线,有人默默擦拭眼角。那位提问的小女孩被老师牵着手离开,临走前回头望了苏照一眼,眼神清澈如泉。苏照冲她点头,心中忽生一念:或许真正的传承,并非靠典籍或法器,而是这样一双眼睛,愿意相信“记得”有力量。
夜幕降临,苏照独自回到居所。这是一间简朴的小院,院中有一口古井,井边立着一块无字石。她说过,等哪天自己也该被记住时,再来刻名不迟。屋内陈设极简,唯有一案、一灯、一蒲团。她盘膝坐下,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卷残页??这是近日从南岭考古队手中接过的战时日记片段,纸张泛黄脆裂,墨迹模糊,但仍可辨认出几行字:
>“三月十七,雨。粮尽,箭折半。兄弟们说笑,若能活着回去,要喝一碗热汤面,加两个蛋……我不知能否归家,只愿有人记得我们曾守在这里。”
落款是一个潦草的名字:“陈小满”。
她闭目凝神,指尖轻抚纸面,共忆之力缓缓渗入。刹那间,画面浮现:一座低矮的哨塔矗立在山隘之间,四周尸横遍野。一名年轻士兵蜷缩在角落,肩头插着半截断矛,怀里紧紧抱着一本破旧账册。他嘴唇干裂,低声数着名字:“李大牛……王二虎……周石头……赵春花……”每一个名字,都是同袍的姓氏与乳名。他说:“我不能全记住了,但我得试试。”
然后是火光冲天,敌军破关而入。他挣扎起身,将账册塞进墙缝,用血涂满整面石壁,写下一行大字:“我们在此战死,但我们不是无名之辈!”
画面戛然而止。
苏照睁开眼,泪水已滑落颊边。她轻轻将残页放入一只陶罐中??这是她近年来养成的习惯:凡未能立即编录入《共忆典》的遗物,皆暂存于此,名为“待忆坛”。坛中共有四十七件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是一段尚未完整拼凑的记忆碎片。
她知道,有些名字,需要更多线索才能真正复活;有些故事,必须穿越谎言与遗忘的层层迷雾,才能抵达真相的核心。
***
次日清晨,一封急报送达。
来自东洲临江城:一处百年老宅翻修时,在夹墙中发现大量信札与兵符,经初步鉴定,属百年前“赤水之战”时期遗物。更重要的是,其中一封密信提及“裴烈未死”,并指出其残部曾秘密退守黑崖洞,意图重组抗敌势力,却因内部叛变遭围剿灭口。信末附言:“吾以性命担保,裴烈之忠,天地可鉴。然今朝权贵讳言此战,恐真相永埋。”
苏照看完,久久不语。
裴烈……那个她在忘川谷唤醒的第一位将军,那个宁死不让名录焚毁的男人,竟然可能还活过一段时间?甚至,他的牺牲并非终点,而是一场更大阴谋的开端?
她立刻召集三位资深承忆使商议。三人皆是她亲授弟子,分别负责北境、西荒与南海的寻忆工作。他们齐聚小院,围坐于井旁。
“若此信属实,”北境使者沉声道,“则意味着‘忘川谷战役’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清洗行动的一部分。不只是抹除战败的事实,更是系统性地铲除所有知情者与抵抗余脉。”
“而且,”西荒使者补充,“这些信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们本该被搜查焚毁,却能在百年后重现人间??说明当年有人刻意藏匿,寄望后人发现。”
南海使者盯着那封密信的笔迹良久,忽然道:“这字迹……我在海底沉船的日志里见过。写作者名叫沈砚,曾任赤水军参军,后被列入‘叛臣录’,家族流放至极南孤岛。据传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待春风渡海,吾言自现。’”
苏照心头一震。
春风渡海……如今正是春末,南方海域光桥再现,八星连珠之象重临。难道这一切,竟是某种冥冥中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