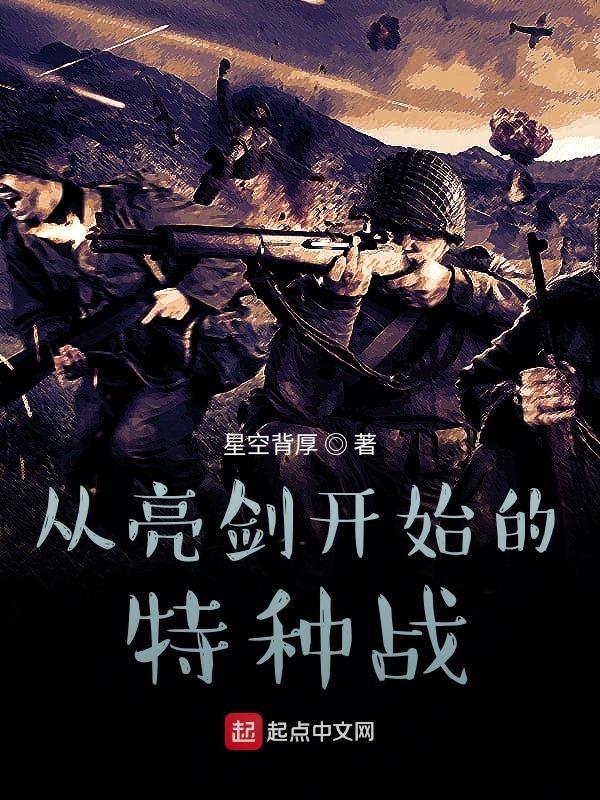我的书库>年登巷陌家家酒 > 第 74 章(第3页)
第 74 章(第3页)
在隔壁街凉粉摊子上,见着剩下几人时,盛达善当真是笑了。
与江大嫂问过一句,他脑袋一扭,看向那几个,“行啊,都来了。”
邓登登老实巴交的点头,“章柏诚和江白圭也在呢。”
盛达善:“……”
他是想问候那两个吗?
甫一见面,说不完的话。
江大嫂称道困乏,说是要回驿馆歇歇,盛樱里哪里不知道她想回去照料,怕江白圭赴宴醉酒,身边连个能端盏茶水的人都没。当也不多劝,只道是他们晚些回去,约莫傍晚。
这刚说罢,谁知江鲫也说要回,缘由说不出个二三来,但盛樱里一肚子官司要问盛达善,委实顾不上盘查多问。
分作两路,各自找地儿去歇。
“我们去哪儿?”盛樱里问。
盛达善走在前头,倒是一副熟门熟路的架势,闻言,懒怠的耷拉着眼皮说:“去鬼混啊。”
盛樱里:“……”
怎的还记仇了呢。
骄阳晒得一个个儿脸红冒汗,盛樱里和乔小乔互相搀扶,邓登登走在旁边,都热得无话。
盛达善却是被自己衣袖上的酒湿熏得头晕,也没走得多远,不多时,抬步进了一间唱楼,要了一间雅厢。
几个小土包子哪里见过这撒银子的地儿,不免环视打量,窗棂推开,正对楼下唱台,伊人扮作角儿,咿咿呀呀唱着白蛇。
“这里很贵吧?”乔小乔问。
“还成。”盛达善应了声,说:“我出去片刻,你们待着别乱跑。”
盛樱里忙着瞧这熏香描金的屋子,很是敷衍的摆摆手,让他忙去。
盛达善推门出去。
“盛二哥是在这儿做生意吗?”乔小乔小声问。
盛樱里摇摇脑袋,她也不知道呢。
只瞧着那厮虽是穿着简朴,但那料子不比她身上的差,想来是过得不苦。
性命无虞,日子无困不苦,那便是极好了,盛樱里求的不多。
几口冰镇瓜果下肚,几人身上的暑气渐渐消散,兴致勃勃的凑在窗前,看台下伶人唱。
盛达善出去片刻,再回来时,身上的酒气散了许多,脸上水珠坠着,衣袖也湿了大半,他浑然不觉难受,就那样穿着湿衣。
倒也非是他愿如此,且不说盛樱里是个大姑娘了,总不好在她跟前衣衫不整,再有,还有别家姑娘在,市井人家虽是没恁多讲究,但也不能明知失礼而为之。
盛达善扫了眼案几上还剩几瓣的瓜果,摇铃又让人送了一盘子来,并几盏冰酥酪。
“说说吧,怎的千里迢迢跑来了这旧京?”盛达善一人占去了一张榻,斜靠着,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盛樱里才不会被他唬住呢,吃一口酥酪,问:“我还没问你呢,你何时来的,是来做什么,与曹家的旧账可算清了?”
她抿了抿唇,咽下了那句“大乔阿姐可知道?”,只含蓄的朝他眨了眨眼。
盛达善哼笑,“还挺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