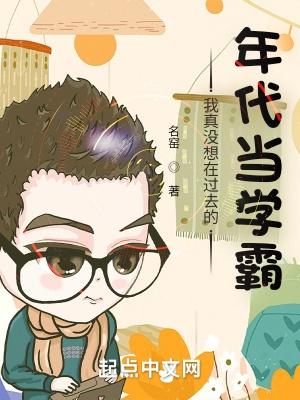我的书库>华娱从洪世贤开始 > 第601章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第2页)
第601章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第2页)
林浩然在此处设计了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摄像机缓缓升起,俯瞰整个广场。灯光渐次亮起,如同星辰落地。背景音乐悄然响起,是由蒙古族老人演唱的长调改编而成的交响版,苍茫辽远,又饱含希望。
影院内外,无数人起身鼓掌。
首映结束时已是深夜。工作人员忙着收拾设备,观众却久久不愿离去。有人自发组织分享会,围坐在银幕下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孩子跑向许兰,怯生生地说:“阿姨,我也想学表演。”她蹲下来,认真看着孩子的眼睛:“那你先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那一刻,她不再是演员,而是桥梁。
林浩然走出人群,独自走到广场边一棵老槐树下。手机震动,是李砚发来的消息:“票房实时统计出来了,全国一百个放映点,平均上座率92%,线上预约观看人数突破八百万。各大平台热搜前十占了七条。有人说,这是十年来最‘不像电影’的电影,也是最像生活的电影。”
他笑了笑,回了一句:“它本来就不该像电影。它就是生活本身。”
正欲收起手机,又一条信息弹出。陌生号码,内容简短:
>“我是当年退学的那个女生。我现在是一家儿童剧团的导演。谢谢你,让我敢回去叫我妈一声‘对不起’。”
他的手指顿住,眼眶发热。
第二天清晨,剧组全员集合在最初拍摄的那所小学操场上。天空湛蓝,晨光洒满青石台阶。林浩然带来了一份新计划书:《普通人?第二季:大地之声》。这不是续集,而是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联合教育部门与地方文化馆,在全国遴选一百个基层故事,由当地居民亲自出演,剧组提供技术支持与传播渠道。
“我们要做的,”他说,“不是继续讲他们的故事,而是教会他们自己讲故事。”
许兰接过计划书,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小字:“所有参演者不分片酬,唯一报酬是??你的名字将出现在credits最后一行:‘主演:我自己’。”
她笑了,眼角泛起细纹。
周小雨走上前,递给每人一枚定制徽章,正面刻着“我说故我在”,背面是一行手写体:“哪怕全世界都沉默,你也值得被听见。”
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缓缓驶入校园。车门打开,跳下来的竟是陈国栋。他摘下头盔,露出额头一道新疤,咧嘴一笑:“听说你们要搞新项目?算我一个。我这几年攒了些钱,够买台二手摄影机。别的不行,架三角架我最熟。”
众人哄笑。
随后几天,报名者络绎不绝。有曾因性别歧视被迫放弃舞蹈梦想的男舞者,如今在工地教工友打太极时融入古典舞步;有盲人按摩师,每天睡前录一段音频日记,坚持了整整八年;还有那位内蒙古的蒙古族老人,带着孙子一起寄来一段父子对唱的民谣,附言写道:“歌声飞得比鹰高,它不会迷路。”
林浩然把这些资料整理成册,命名为《未命名档案》。他在扉页写下:“艺术从不诞生于殿堂,而生长于泥土之中。只要根还在,春天总会来。”
与此同时,《第四部曲:普通人》正式通过审查,并获得国家电影局特别推荐。官方评语写道:“该片以朴素之姿承载厚重人文关怀,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精神,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新突破。”春节档公映当天,票房逆势上涨,豆瓣开分9。8,猫眼评分9。9。媒体称其为“国民心灵史诗”。
然而,真正的胜利不在数据,而在人心。
北京某心理援助中心反馈,影片上映一周内,热线来电量增加370%,许多来电者都说:“我看了《普通人》,第一次觉得,原来我的痛苦也有人懂。”一所重点高中因此开设“倾听课”,鼓励学生每周写下一封“给世界的信”,并轮流在班会上朗读。一位家长感慨:“以前总嫌孩子话多,现在才发现,他们一直等着有人听。”
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位曾三年未出门的抑郁症患者再次发来邮件。这一次,他附上一张照片:阳光洒在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手里捧着一本书,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文字只有一句:
>“我开始写东西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但我想试试。因为你说过,存在就够了。”
林浩然打印了这张照片,贴在剪辑室的墙上。下面写着:“致每一位不敢开口的人。”
项目推进顺利,但挑战依旧存在。某日,一家主流电视台邀请林浩然参加访谈节目,主题本为“现实题材的崛起”。可录制中途,主持人突然转向:“林导,您强调真实,可是否考虑过,过度渲染苦难会引发观众焦虑?有些人觉得,看您的电影太累,不如刷短视频轻松。”
现场气氛瞬间紧张。
林浩然沉默片刻,反问:“请问,如果我们连呈现真实的勇气都没有,那娱乐的意义又是什么?难道艺术的责任不是照亮黑暗,而是帮人们逃避光明吗?”
主持人语塞。
他继续说道:“我不否认轻松作品的价值,但请允许有些电影,是为了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而拍的。累?是的,因为它触碰了我们共同回避的痛。可正因为累,才说明它真的碰到了伤口。而治愈的第一步,从来不是假装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