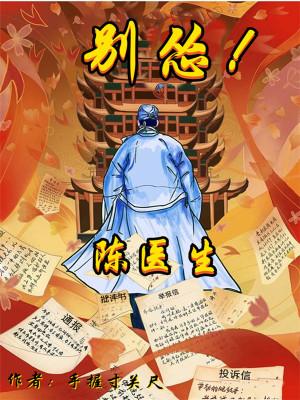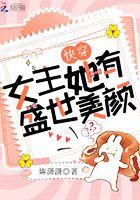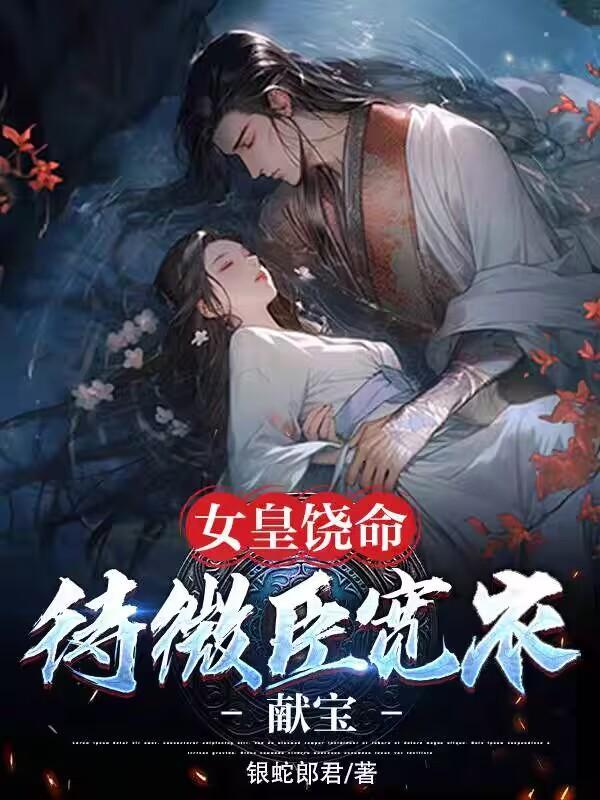我的书库>晋庭汉裔 > 第二十二章 杨难敌抵达(第1页)
第二十二章 杨难敌抵达(第1页)
次日晌午,河东军身在渭南望楼上,果然看见有大批军队赶赴长安。
这支军队打着征西军司的旗号,高擎白虎幡,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如林的白虎幡之中,同时高挂有黄底红字的阎字旗、张字旗,中间甚至高挂有红底黑。。。
雪片如絮,纷纷扬扬落于铁甲之上,融成细水流下。卢景一动不动,仿佛与战马凝为一体,矗立在风雪之中。身后十万大军屏息以待,唯有旗帜猎猎作响,似在回应天地间的肃杀之气。长安城头的晋旗终于断了绳索,飘坠城下,被积雪掩埋。那一刻,无人下令,却有千人低呼:“降了!他们挂白布了!”
卢景缓缓收回长剑,轻声道:“传令??缓进,列阵而行,不许喧哗,不许驰骋。今日我们不是攻城者,是归人。”
号角三声低鸣,大军徐徐推进。沿途百姓自屋中探出头来,颤抖着点燃灯笼,一盏、两盏……连成星河。老人跪于门前叩首,孩童被母亲抱起指向军中帅旗,低声念着“卢公来了”。有人捧出热粥置于道旁,有人焚香祷祝,泪流满面。一名老儒踉跄而出,手持残破《论语》,颤声诵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死无憾矣!”
卢景下马步行,亲自扶起老者,解下披风为其裹身。他声音不高,却清晰传遍街巷:“诸位父老,我卢景带兵北上,非为征服,只为回家。这长安,从来不是敌城,是我们祖宗魂灵安息之地。”
消息如风,一夜传遍九衢。次日清晨,四门大开,留守官员率百官白衣素服,捧印绶、户籍、仓册,跪迎于朱雀大街。卢景未入宫城,先至太庙旧址。荒草掩映间,仅存石阶数级,碑文剥蚀难辨。他整衣正冠,焚香三拜,将南郑黄土洒于基前:“列祖列宗,子孙景奉命归来,虽迟,未敢忘也。”
当日下午,卢景暂居太极殿西阁。此殿久废,梁柱蛀朽,唯地砖尚存汉时纹样。他命人清扫除尘,不许更换一物。入夜,孤灯独坐,展阅缴获之晋廷密档。其中一份奏疏赫然入目:王衍曾密令关中诸将,“若南军入境,可引黄河水灌野,毁田焚粮,宁使赤地千里,勿资敌粒粟”。
卢景指尖微颤,良久闭目。片刻后提笔批曰:“昔秦坑赵卒,天怒人怨;今晋欲屠民以拒义师,其罪更甚。然我既承天命,当以仁覆天下,不可效彼暴虐。”遂下令:“即刻遣使巡视渭北各县,凡因焦土令受害之家,一律登记造册,免赋五年,每户赐种牛一头、粟米十石。”
第三日,开朝议政。卢景不设龙椅,仅置一案于殿中,邀旧晋文官共商善后事宜。裴绰自岭南遣使至,献《安陕策》七条,首条即言:“收人心莫先于恤亡、录忠、赦罪。”卢景深以为然,当即颁布三令:一、为刘琨父子建祠于晋阳故地,追赠忠烈侯;二、赦免所有临阵倒戈或闭城不战之晋将,原职留用;三、凡曾匿藏典籍、保护学士之士人,不论出身,皆授文林郎虚衔,月俸由国库支给。
最引震动者,乃对陆昀之处置再议。有臣谏曰:“此人纵火毁书,罪不容诛,岂可宽宥?”卢景却道:“典籍可焚,心火难熄。他烧的是竹简,我若杀他,烧的便是人心。”遂亲赴敦煌书院,见陆昀正立台前讲《孟子?梁惠王》,声如洪钟,鬓发尽白。讲毕,二人相对无言。良久,卢景从袖中取出一部手抄《春秋》,乃其幼年随傅畅所习之本,扉页犹有批注真迹。
“这是我祖父卢志当年逐字讲解之书,”卢景轻放案上,“你若觉得我伪饰仁义,不妨继续骂。但请一边骂,一边教。让下一代知道什么是真儒,什么是假道。”
陆昀怔立良久,忽伏地痛哭:“我恨你篡权,可……可你做的事,却是历代帝王都不曾做的。”
卢景扶他起身:“我不是要做帝王,是要做执炬者。黑暗太久,总得有人点灯。”
长安初定,民生亟待复苏。崔嶷率工部官吏昼夜勘测,提出重修郑国渠计划。卢景亲赴泾水源头踏勘,见渠道淤塞、闸门崩塌,慨然道:“秦以水利富国,汉因农桑兴邦。今我复汉室,当先兴水利。”下令征发闲散兵卒五万,以工代赈,疏通主干渠三百余里,并设“渠丞”专职管理,严禁豪强私截水源。百姓闻之,争相投役,仅三月便完成一期工程,渭水平原万亩旱田变为沃野。
与此同时,陈烈自洛阳方向传来捷报:司马?兵败被俘后拒不投降,然目睹卢军救治伤卒、抚恤遗属之举,终叹曰:“吾辈为权贵效命半生,未曾见如此仁师。”遂自愿写下劝降书,致仍在抵抗之晋军将领十余人。半月之内,函谷关以东十七城望风归附。
然亦有暗流涌动。某夜,卢景巡城归邸,忽觉庭院异样??檐角瓦当松动,窗纸微裂。薛兴疾步上前,一脚踢开寝门,空室无人,唯案上茶盏尚温,杯底压着一枚铜钱,正面刻“永兴”二字(晋怀帝年号),背面凿“弑君”血痕。
卢景凝视良久,冷笑:“王衍这是逼我称帝啊。”
原来,建康方面已有风声,谓卢景“挟胜而不登大位,必有异志”,江南士族观望踟蹰。更有流言称其“实为匈奴养子”,妄图颠覆华夏正统。卢景召傅畅密议,老人拄杖叹息:“名不正则言不顺。你已行天子事七年,再推让,反成虚伪。”
于是腊月初八,冬祭太庙。卢景率百官献牲告祖,宣读《即位诏》:“惟建兴七十九年,岁在辛酉,朔风振岳,天命更新。朕以菲德,承累世之遗绪,赖将士用命,士民归心,克复旧都,肃清氛?。今谨遵高皇帝受命之符,恭膺大宝,国号仍称‘汉’,改元‘兴宁’,大赦天下。”
礼成之际,忽闻钟鼓齐鸣,原已锈蚀三百年的景阳钟竟自行震荡,声闻数十里。百姓奔走相告,谓“天心感应”。卢景立于丹陛之上,望着漫天飞雪化作晴光,只觉肩头千钧卸去,又添新担。
翌日早朝,首议谥法。群臣请追尊卢志为太祖,卢景摇头:“我卢氏虽历仕魏晋,然真正开创基业者,乃南郑立国之初那些饿着肚子修城墙、扛着锄头打蛮夷的百姓。若要立祖,当以‘民’为始。”最终定议:追尊“无名黎庶”为“协熙公”,立碑城南,铭曰:“国有疆,民无名;功在社稷,荫及子孙。”
新春将至,卢景命宫中不张彩灯,反开仓放粮。正月初五,亲率皇子卢承、义子卢念民赴城郊难民棚户区,挨户送炭、发棉衣。一户寡妇泣诉丈夫死于晋军拉夫,幼子病重无药。卢景当即解下玉带换药,并令太医署设立“疫疠所”,专治贫民疾病。
元宵之夜,百姓自发集于朱雀街,以冰雕成灯,刻“兴宁”字样,中间簇拥一尊泥塑??正是卢景蹲身为老兵系鞋带之像。卢念民见之,哽咽道:“爹,他们把你当神了。”
卢景摇头:“我不是神,只是还不敢忘记自己也曾饿过饭的人。”
二月,张弘自陇右来报:凉州牧张峻病逝,临终托孤于侄儿,举州归汉。卢景为之辍朝三日,亲写祭文:“张公守西陲三十载,外抗胡虏,内抚流民,使丝路不绝,文明不坠。此等功业,不在开疆,而在持节。”并敕封张峻为“武襄侯”,子孙世袭罔替。
至此,关陇悉平,河北犹战。卢景知王衍困守洛阳,必作困兽之斗,乃召集众将布防。他指着地图道:“司马?虽败,然晋军主力尚存河南。若我贸然东进,恐其决黄河以阻我师。”遂采纳崔嶷奇策:命工匠打造数千木筏,暗藏火药于中,顺流漂下,在洛阳下游择机引爆,冲毁预设堤坝,反使其“水攻”自溃。
同时,派遣细作混入洛阳,散布谣言:“王衍欲携珍宝南逃,已备舟船千艘。”又伪造其女书信,言“父谋害宗室以固权位”。城中本就粮尽人相食,闻讯哗变,禁军统领当场斩杀监军,开城迎降。
三月初三,上巳节。卢景率军入洛阳,直趋邙山。于汉光武帝原陵前下拜,清除杂草,重立碑石。他对左右道:“古人云,‘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里埋着我们的根。谁忘了祖先,谁就不配领导这个民族。”
随后,他下令将王衍囚于金墉城,不予加害,但每日派人送《贞观政要》一部,令其研读思过。王衍起初狂笑,继而沉默,终日抄写“水能载舟”一句,反复不已。
四月中旬,南方局势突变。会稽谢氏联合顾、陆、朱、张四姓,果然起兵讨伐王导(王衍之弟),控制江东八郡,遣使奉表归汉。卢景接书落泪:“谢家郎终究没有辜负那封蜜蜡信。”遂封谢?为“会稽公”,其余士族按功授爵,但明令:“江南土地,不得私占万亩以上,违者削爵。”
五月,交州刺史上报:扶南国遣使进贡珊瑚、象牙及南洋奇书七十二卷,愿通商路。卢景览书大喜,发现其中竟有失传已久的《齐民要术》残卷。立即下令组建“译经馆”,招募西域僧侣、波斯商人、南洋学子共同整理,题名为《海汇文明录》。
六月初六,三年一度的科举首次在长安举行。考生不分贵贱,只要有识字能力即可报名。试题由卢景亲拟:第一场策问《如何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第二场论《律法与皇权孰重》;第三场诗题《春风吹过潼关》。
放榜之日,榜首乃一盲女,名柳含烟,其策论中有句:“王者之政,不在高山筑台,而在低处开门。”卢景亲自接见,授翰林院编修,特许其以口述代笔,由专人记录。
秋分时节,卢承年满十六,正式加冠。卢景赐其佩剑,名曰“守心”,并在家宴上郑重说道:“你将来若掌兵权,记住三件事:一不杀降,二不毁学,三不在饥年征税。能做到,才配站在这座城里。”
同年冬,全国户籍统计完成:人口一千二百六十万,较七年前增长四成;垦田面积突破八千万亩;官办学校达三千七百余所,学生逾二十万。卢景看着账册,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这才刚刚开始。”
兴宁二年元旦,卢景登太极殿受贺。百官山呼万岁,海外诸国皆遣使朝觐。日本遣唐使跪献《倭国风土记》,波斯商人带来琉璃灯,龟兹乐师奏响《月照龟兹》。当各国使节退下后,卢景独自留在殿中,望着梁上newly修复的彩绘??那是画师依照古籍复原的未央宫图样。
他轻轻抚摸座椅扶手,低声说:“父亲,母亲,祖父……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真的回来了。”
窗外,春风拂过长安城头,鼓楼双钟再次齐鸣。这一次,不再是祈愿,而是宣告。
一个断裂的文明,正在重新接续它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