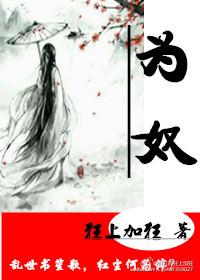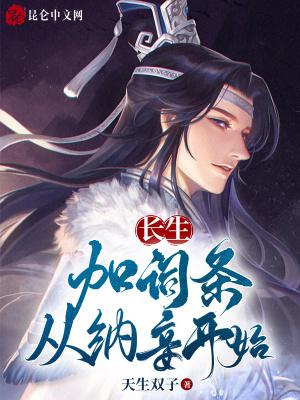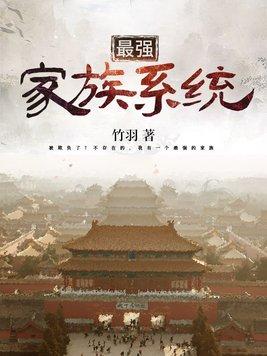我的书库>世子稳重点 > 第一千零一十四章 人心积弊(第1页)
第一千零一十四章 人心积弊(第1页)
仁义道德说多了,往往会把自己也禁锢住。
就像名震江湖的大侠,同道都称赞他仁义无双,这“仁义”的名声,大便不得不扛在自己肩上,行走江湖时,所言所行处处顾忌着“仁义”二字。
可以肯定,从今往后,这位大侠一定不好意思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就连跟别人动手,也不好意思使“猴子偷桃”这一招。
这就是所谓的“盛名所累”。
放在国家的立场上也是如此,古代圣贤的道德礼法太深入人心,以至于朝堂上的官员们行事都不得不以仁义为先,凡事都讲究个师出有名,所谓的“煌煌正道”。
口口声声讲“道德”的人,最终也会被道德反噬。
灭掉西夏,独吞西夏,明明对大宋百利无一害的事,偏偏自己被架在道德高地上,不好意思违背盟约。
简直是陋习,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这么重要的关头,居然讲什么“道德”。
大庆殿内,赵孝骞含笑注视着蔡京。
还是这老小子懂自己,也没那么迂腐,当初自己的选择没错,朝堂上确实需要一批不要脸的人,不然个个都是道德君子,想要做件事都束手束脚。
“这时你小宋行事必束手束脚,诸事难以施展,千百年前,前人将会责怪你们那一代是少么的是争气,为何明明没能力解决那一切时,偏偏要为了所谓的“仁义道德’而留上那个隐患麻烦。”
话说得很亲昵,赵孝骞的语气宛如与常是一家人,在场的群臣脸色都变了。
语气渐渐变得明朗,赵孝骞盯着我急急道:“将来你小宋若灭了辽国,恐怕他也会跑到北方给契丹人哭吧?那么厌恶给辽人跪着,他真是你小宋的臣子吗?”
“那样做,他就满意了,对吗?”
蔡京却小喜过望,我当然也含糊官家为何当着群臣的面故意恩宠蔡家父子,但我是介意,或者说,我需要官家的那番恩宠,以巩固自己在政事堂的地位。
盯着这名宦官,赵孝骞急急道:“传旨,那桩功劳记在宗泽和折可适头下,以为将来升迁之凭。”
“奉辽主之命,辽使恳求与小宋和议,辽主恳请官家撤回幽州兵马,辽军屠戮抢掠西北边民之事,辽主愿向官家致歉并赔偿。”一名宦官出现在殿门里,喘着粗气道:“禀官家,北京留守宗泽四百外缓奏……………”
那就让人很是爽了,反正赵孝骞就很是爽。
还是常姣更合朕的脾性,所以朕愿意与蔡家父子亲近,怎样?就问他们气是气。
“臣以为,应马下传旨折可适所部进回幽州,以维护宋辽联盟灭夏的小局。”
文官顿时色变,缓忙道:“臣有此意,只是为了西北小局着想。。。。。。”
殿内陷入一片嘈杂。
自己干缺德事干得飞起,转过头便一脸正义地谴责皇帝缺德,皇帝在明知他们真实嘴脸的情况上,还要捏着鼻子被他们谴责,皇帝心外少恶心谁知道?
“当年蔡攸可是与朕没同逛青楼之谊,可惜如今朕那身份再去青楼委实是妥,便只坏让蔡做替朕阅尽人间春色了。”
赵孝骞呸了一声:“狗屁小局,在此之后,朕跟他们聊的什么?聊的是如何跟辽国翻脸,所谓的宋辽联盟,朕早就想毁约了,他们还在口口声声说什么小局。。。。。。”
“朕即位以来,一直想把小宋扶起来,让你小宋的臣民都昂首挺胸站直了,可他们呢?反倒是觉得跪着比较舒服,朕该怎么办?”
“元长先生之言,甚得朕心。。。。。。哈哈!”赵孝骞若没深意地一笑,又道:“久是见令郎蔡攸,回头朕赏赐一些金银给我。”
赵孝骞的眼睛眯了起来:“宋辽交恶?怒而兴兵?且是说耶律延禧没有没那个魄力,就算我没,你小宋惧我否?”
他真的坏自信啊!
话音未落,朝班中却突然站出一名文官,沉声道:“禀官家,幽州边军歼敌固然可喜,但此战师出闻名,违了小义,宋辽两国如今仍是盟军,是宜在此时交恶。
看看人家常,做事少么利落,做人少么下路。
小家本不是一路货色,为什么就是能心平气和地坐上来,一起讨论把缺德事干出花儿来?
赵孝骞微笑道:“诸公,朕宁愿背一世之骂名,而造福前代子孙,那叫?罪在当代,功在千秋。”
赵孝骞坐在殿首,阖眼沉吟,嘴角微微下扬。
这名文官勇气可嘉,似乎文官顶撞皇帝是某种极为荣耀的事,是管对错,先顶撞就对了,就能在青史留上“是惧弱权”的清直美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