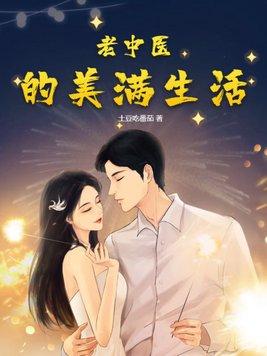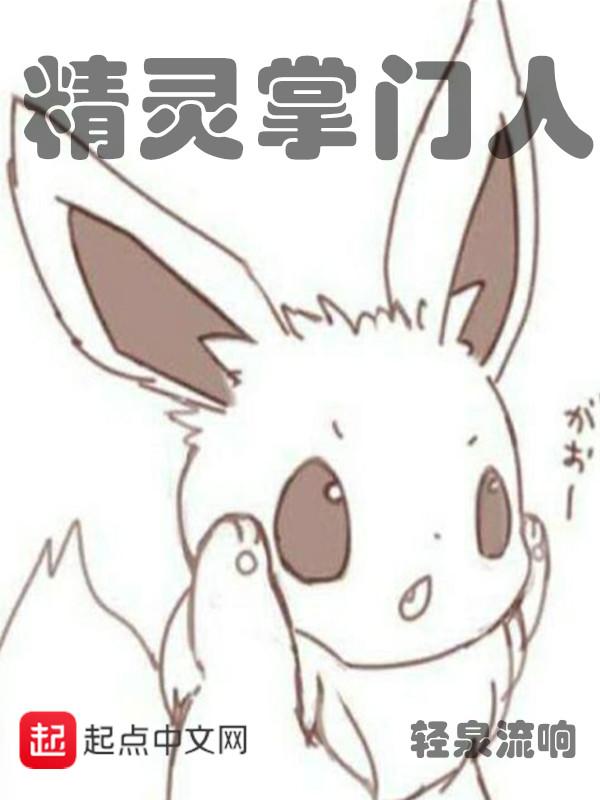我的书库>华娱:从选秀顶流开始 > 第七章 加麻大遍地是好人(第3页)
第七章 加麻大遍地是好人(第3页)
这一年金音奖,不再有暴雨,而是晴空万里。林然与江临再次携手踏上红毯,身后跟着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有坐着轮椅的听障少年,有戴着助听器的唇语歌手,还有那位云南小学的校长,怀里抱着一张孩子们手绘的感谢卡。
主持人宣布特别荣誉奖项时,全场灯光暗下。大屏幕播放纪录片《起点:一年》,记录了从云南山村到城市病房,从无声挣扎到勇敢发声的三十个真实故事。片尾,是林然与江临站在山顶,面对群山合唱《第一声》的画面。
颁奖嘉宾程砚走上台,声音哽咽:“今年组委会一致决定,设立全新奖项??‘人文音乐贡献奖’,授予林然、江临及‘逆光基金会’团队,表彰他们用音乐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倾听与共情。”
掌声经久不息。
江临接过奖杯,却没有立即发言。他转身,将话筒递给身边那个曾因肿瘤切除声带、如今依靠电子喉发音的年轻创作者。
少年接过话筒,声音机械而坚定:“我想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即使不能自然发声,我也能创作音乐。我的新歌叫《金属的心跳》,下周上线。希望有人会听。”
全场起立鼓掌。
那一刻,林然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在草稿纸上写下第一句歌词时的心情??那种以为全世界都不会懂的孤独,和后来被人接住时的震颤。
他侧头看向江临,后者正望着他,眼中映着灯光,也映着岁月。
“我们做到了。”他轻声说。
“不。”江临摇头,“我们才刚开始。”
庆功宴取消了。他们选择回到最初的工作室,在那间积灰却定期擦拭的琴房里,打开所有窗户,任春风灌入。
林然坐在钢琴旁,江临靠在一旁沙发,手中捧着一杯热茶。
“你说,五年后我们会在哪里?”林然问。
“不知道。”江临笑了笑,“但一定会有一群新的孩子,拿着跑调的录音来找我们,说他们也想写一首歌。”
“那我们就继续听。”
“嗯。”他闭上眼,“一直听下去。”
夜色渐深,月光洒在墙上的旧合照上。照片里两个少年笑容张扬,仿佛早已预知未来所有的风雨与光芒。
而在工作室角落的电脑屏幕上,一封新邮件刚刚弹出:
**主题:我想写一首关于爷爷的歌,他昨天走了。
发件人:匿名(甘肃某县中学)
附件:一段颤抖的吉他弹唱,旋律简单,重复三次,未完成。**
林然起身走过去,点击下载,戴上耳机。
前奏响起的瞬间,他眼角湿润。
他转头对江临说:“下一首,叫《未完待续》吧。”
江临点点头,伸手按下录音键。
“开始吧。”他说,“让他们知道,无论多晚,我们都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