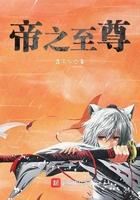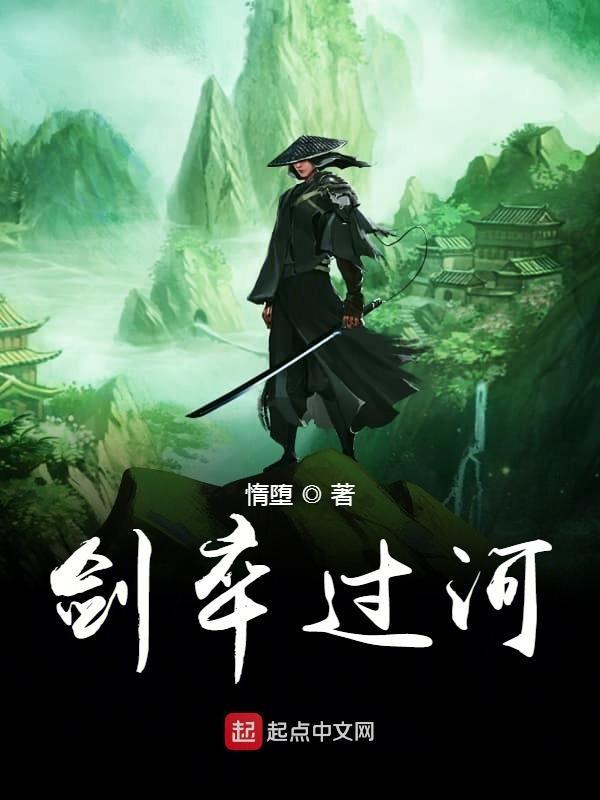我的书库>谁说我是靠女人升官的? > 322刺杀苏陌的真凶八千字大章(第3页)
322刺杀苏陌的真凶八千字大章(第3页)
十年过去。
赤薯已成为主粮之一,与稻麦并列。民间谚语云:“早吃米,午吃面,晚吃薯,梦不乱。”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真人薯”不是神仙给的,是苏家村那位不说话的婆婆和她的徒弟们一锄一锄种出来的。
边境安宁,梦疫绝迹。但阿禾始终没有放松警惕。每年冬至,她仍带领弟子举行“还梦祭”:焚烧写满谎言的纸条,包括“天上会掉饭团”“贵人自会救我”“我不努力也会成功”……
火焰腾起时,众人齐声低语:“我知我醒,我不信谎。”
直到某年冬至,火光映照之下,一名盲童忽然开口唱起一支无人听过的歌谣,旋律凄美,歌词却是古语:
>“铃碎兮土中藏,
>薯生兮照幽茫。
>母血化泥兮养万姓,
>子心蒙尘兮唤不响。”
歌声落下,全场寂静。
阿禾浑身剧震??这首诗,分明出自《梦语录》失传的第五卷!而那孩子从未受过教育,甚至不知文字为何物。
她冲上前抱住他:“你从哪儿学的?”
孩子摇头:“不是学的。它一直在我心里,像心跳一样。”
那一夜,阿禾彻夜难眠。她终于确认了一件事:苏府的意识并未完全消散,而是通过赤薯的根系、通过千万人的劳动与饥饿记忆,悄然编织成一张无形之网,潜移默化地修复着被梦匠腐蚀百年的集体心灵。
这不再是个人觉醒,而是一场文明层面的**自我免疫**。
又三年,西北边陲出现一座新兴村落,全村居民皆聋哑,却人人能耕善织,且每户门前立一小碑,刻四字:“吃真饭者”。学者前往考察,发现他们发展出一套独特手语系统,核心词汇竟是“怀疑”“疼痛”“亲手”“等待”。
更惊人的是,该村儿童天生具备某种能力:能感知他人是否说谎。表现方式各异??有人瞳孔收缩,有人皮肤泛红,有人会无意识模仿对方小时候的动作。
专家无法解释,只好归为“群体性心理感应”。
唯有阿禾明白:这是“醒潮”的进化。当足够多人选择真实,人类本身就开始演化出识别虚假的本能。
她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巡行天下,走到敦煌石窟,在那幅壁画前静坐七日。第七天黄昏,她用尽力气爬上高台,取出发间一枚银簪,轻轻划过画中女子的手掌。
鲜血渗出,顺着赤薯流淌,竟与壁画融为一体。
刹那间,整座石窟震动,沙尘簌簌而下。待烟尘散尽,人们发现壁画变了??女子脸上浮现出模糊五官,赫然是苏府的模样。而她脚下的土地,已延伸成万里田野,无数男女老少正在耕作,每个人背后都隐约浮现一道光晕,形如断裂的锁链。
当晚,万里星空格外明亮。天文监记录到异象:北斗第七星骤然增亮,持续整整一夜,随后缓缓暗去。
民间传言:那是苏府的最后一声铃响。
阿禾回到苏家村时,已油尽灯枯。她在师父墓前坐下,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封面无字,内页空白。她以指蘸血,写下最后八个字:
>**种下疑问,即是光明。**
然后合眼微笑,安然离世。
村民们依其遗愿,将她葬于赤薯田中央,不立碑,不刻名,只在四周种满薯苗,形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形状。
多年后,有旅人路过此地,见田中有异:每逢月圆,薯藤自动排列成行,组成一行行文字,内容各不相同,有时是农谚,有时是警句,有时竟是远方发生的新闻。
当地人笑着说:“这是‘问田’,夜里会自己写字。你想知道什么,就来种一季,或许能得到答案。”
而最令人费解的是,某些深夜,若有心人俯耳贴近土地,竟能听见极其微弱的声音,像是无数人在低声重复一句话:
>“这顿饭,是谁种的?”
没有人能确定这声音来自地底,还是来自倾听者自己的心底。
但每个听到的人,从此再没能心安理得地吃完一顿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