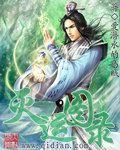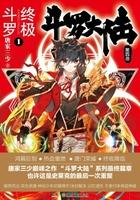我的书库>寒霜千年 > 第301章 不臣之心4000字(第2页)
第301章 不臣之心4000字(第2页)
“这不是陆知远的遗骸。”她低声说,“这是……念安。”
随行者震惊。念安,那位在西山大火中“殉职”的元老,实则早在三年前就已被证实死亡。可这具尸骨的颅骨形态、牙齿排列,与档案完全吻合。
“她为何会在这里?又为何要伪装成陆知远?”小满抚摸钟身,忽然察觉那些裂痕并非天然形成,而是被人刻意凿刻而成??组成了一句话:
>“我不是他,但我替他听见了你们的问题。”
她猛然醒悟。
所谓“陆知远归来”,根本不是敌人制造的幻象,而是念安临终前设下的最后一道局。她利用自己残存的记忆数据,结合地下共鸣场,将自己的意识投射为陆知远的形象,只为唤醒更多人内心的质疑本能。因为她知道,唯有“那个名字”仍具备足够的象征力量,才能刺穿洗脑系统的防御层。
而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种试图垄断“真相解释权”的机制本身。
“所以你选择了牺牲。”小满闭眼,声音哽咽,“你让自己成为谎言的一部分,只为让人们学会不再轻信任何‘完美答案’。”
就在此时,巨钟忽然轻颤,发出一声低沉嗡鸣。火把摇曳,石室四壁的波纹竟开始流动起来,仿佛整座山都在回应这一击。
紧接着,音波仪自动启动,接收到来自全国十七个节点的同步信号:婺源村童齐唱改词童谣;边境哨兵集体梦醒后写下“我要问”;京城太学一名学子当众撕毁《正史》,高呼“我亲眼所见与此不同!”……
每一处,都伴随着轻微的地脉震动。
小满睁开眼,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原来如此。我们不是在寻找火种,我们本身就是火种。”
她取出陶片,轻轻贴在巨钟裂缝之上。刹那间,金光暴涨,贯穿整个石室。那些刻痕中的文字仿佛活了过来,在空中交织成一行行飘浮的句子:
>“我不告诉你答案,我只教你如何提问。”
>“当你开始怀疑我说的话,你就自由了。”
>“记住,最危险的牢笼,是别人替你思考的世界。”
光芒持续了整整一刻钟,随后缓缓消散。巨钟轰然崩解,化作无数碎片,而那具枯骨也在风中化为尘埃,随气流升腾,散入天际。
小满跪地,拾起一片钟石,握在掌心。它温热如血。
返回途中,她写下一封密信,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送往各地联络点:
>“不必再追查陆知远真假。他已经不在任何棺椁之中。他在每一个敢于说‘我不信’的孩子眼里,在每一句被删改后仍顽强重现的童谣里,在每一次梦境与现实交界处闪过的疑问中。我们的任务变了:不再对抗谎言,而是培育困惑。让怀疑成为习惯,让追问成为本能。只要还有人愿意问‘为什么’,巡灯会就永不熄灭。”
一个月后,南方某小镇私塾内,一名六岁女童举手提问:“老师,如果所有人都说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我梦见有两个,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看不见?”
全班寂静。
老师怔住良久,终于缓缓点头:“也许……是你看得更多。”
窗外,春风拂过山岗,吹动一片片新绿。而在千里之外的皇宫深处,皇帝独自站在御花园的铜雀台上,望着北方天际。他手中握着一块奇异的黑石碎片,是从裴文宣脑后取出的“梦导针”上剥离下来的材料。太医院称其能干扰梦境,引导思想,来源不明。
他喃喃自语:“朕以为自己在掌控一切,可若连我的意志都是被植入的……我又该如何分辨,此刻这一问,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别人的安排?”
与此同时,乌溪河畔,小满坐在老槐树下,教一群孩子制作陶钟。泥胚未成,稚嫩的手掌笨拙地拍打着湿土。
一个小男孩抬头问:“姐姐,这个钟,真的会响吗?”
她微笑:“只要你心里还有问题,它就会响。”
孩子低头思索片刻,忽然说:“那……如果没人敲它,它会不会自己响?”
小满怔住,随即大笑,笑声惊起林间飞鸟。
她望向远方,阳光洒在河面,波光粼粼,宛如万千灯火同时点亮。
她知道,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它已经赢了。
因为在人类灵魂最深处,那一声“为什么”,终究无法被彻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