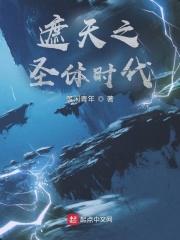我的书库>出宫前夜,疯批帝王后悔了 > 第465章 你这人好坏呀(第2页)
第465章 你这人好坏呀(第2页)
佑安的字迹则更为沉稳:“母后安好。新政推行顺利,户部奏报今年粮产增三成,百姓安居乐业。儿每日省览奏章,不敢懈怠。惟愿您在江湖逍遥,勿念朝堂琐事。待春暖花开,或可携弟妹北上探望。”
晚余读完信,久久不语。沈长安递来一碗热茶,问:“想他们了?”
“怎么会不想。”她轻叹,“但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就像我们一样,终究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冬去春来,山谷回暖。他们在屋前种下数十株梅树苗,又引来山泉灌溉。某日清晨,晚余正在院中煮茶,忽见一只白鸽飞落檐角,脚上绑着一封密信。她取下展开,脸色骤变。
“怎么了?”沈长安快步走来。
她递过信纸,声音微颤:“皇后……死了。”
信中言,幽禁冷宫两年的前任皇后林氏,日前吞金自尽。临终前留下遗书,承认当年伪造遗诏之事确有其事,且幕后另有指使??竟是早已退隐的先帝老师、当朝太傅李崇文!
此人曾为祁让启蒙师傅,权倾一时,后因党争失势归隐南山。谁也没想到,他竟暗中操控皇后多年,意图借妇人之手重掌朝纲。
“他想翻盘。”沈长安冷笑,“可惜晚了十年。”
晚余沉默良久,终是提笔写下一函,命飞鸽传书回京:“厚葬皇后,依嫔礼下葬,不得羞辱尸身。另,请新帝彻查李崇文过往罪证,若有实据,依法论处,不得牵连无辜。”
“你不恨她?”沈长安问。
“我若恨,便与她无异。”她放下笔,望向窗外初绽的梅花,“权力使人疯狂,但她也是被野心吞噬的可怜人。若非李崇文蛊惑,她或许只是个不甘寂寞的深宫女子罢了。”
数日后,京中信使赶到,带来更惊人消息:李崇文被捕当日,竟服毒自尽于堂前。然而在其书房密室中,搜出大量往来书信,不仅证实其操纵后宫、勾结藩王之罪,更揭露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
当年构陷沈家“通敌案”的真正主谋,正是李崇文!因沈父曾在科举案中揭发其贪墨劣迹,故怀恨在心,借边关战事失利之机,罗织罪名,致使沈氏满门遭难!
沈长安握信的手剧烈颤抖,眼中泛起血丝。晚余轻轻抱住他,低声说:“真相大白了。你不必再背负‘逆贼’之名,你的父母兄妹,都可以瞑目了。”
那一夜,他在父母坟前焚香祭拜,将李崇文的罪状一一念诵。火光照亮孤坟,风吹散灰烬,仿佛百鬼齐哭,终得解脱。
春深时节,山谷百花盛开。晚余开始教附近山村的孩子识字读书。她没有自称“太后”,只说是“一位走过很多地方的先生”。孩子们围坐在梅树下,听她讲《诗经》里的爱情,讲《史记》中的忠义,讲天下有多大,人心有多复杂。
沈长安则每日晨起练剑,午后授徒。一些慕名而来的少年侠客拜入门下,他也不拒,只说:“习武非为逞凶斗狠,而是为了守护心中所爱。”
某日黄昏,晚余在溪边洗衣,忽闻远处传来熟悉的童谣歌声。她抬头望去,只见梨月和佑安并肩走来,身后跟着徐清盏与几名侍卫。
“娘!”梨月飞奔而来,扑进她怀里,“我们来看您了!”
佑安躬身行礼,眼中含泪:“母后,我想您了。”
晚余抱住两个孩子,泪水夺眶而出。“怎么都来了?朝中事务怎么办?”
“我已经可以独立理政。”佑安微笑,“而且,我答应过您,等春天来了,就带妹妹来看您种的梅花。”
当晚,一家人围坐篝火旁。梨月兴致勃勃地讲述她如何独自带队巡边,吓得走私马帮落荒而逃;佑安则说起最近修订律法的心得,引得沈长安频频点头。
“你们都长大了。”晚余看着他们,感慨万千,“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事,不是执掌朝政六年,而是养大了你们。”
次日清晨,晚余带着孩子们来到沈家祖坟。她指着那块无字碑,郑重说道:“记住这个地方。它提醒我们,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你们身为帝王将相之后,更要懂得敬畏民心,珍惜和平。”
梨月肃然应诺,佑安更是跪地叩首,立誓不负教诲。
三日后,孩子们返程。临别之际,佑安忽然转身问道:“娘,您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