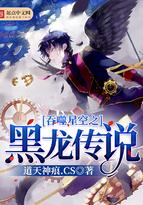我的书库>重生:我老婆是天后 > 第1133章评估二(第2页)
第1133章评估二(第2页)
张浩抬起头,眼里蓄满泪水。
“你知道吗?”林妍说,“你是我们收到的第104个录音。”
张浩愣住了。
“编号104,”她微笑,“而且,你不是第一个男生。”
他怔住:“还有别人?”
“有。”林妍点头,“去年广西有个十四岁的男孩,被亲戚长期猥亵,他录下了对话;前年内蒙古有个高中生,被教练以‘体能训练’为由实施侵害,他也站出来了。他们和你一样,一开始都觉得‘这事不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他们是男孩,因为他们‘应该坚强’。”
她顿了顿,声音更轻了些:“可伤害不会因为你是男孩就减轻一分。痛苦也不会因为社会偏见就自动消失。”
张浩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这一次,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终于有人告诉他:**你的感受是真的,你的伤痛值得被看见。**
“你想报警吗?”林妍问。
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摇头:“我还……不敢。”
“没关系。”林妍说,“我们可以先帮你做心理干预,也可以匿名提交证据备案。只要你准备好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启动司法程序。我们会一直陪着你。”
就在这时,车外传来脚步声。
帘子掀开,范真真走了进来。
她比视频里看起来更瘦,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明亮如炬。她一眼就看到了张浩,走过去蹲下,与他平视。
“你是张浩?”她轻声问。
他点头,嘴唇微微颤抖。
范真真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手腕:“谢谢你录音。你知道吗?每一个按下录制键的人,都在为这个世界点亮一盏灯。你不是软弱,你是勇敢。”
张浩终于忍不住,伏在膝盖上哭了出来。压抑了半年的情绪如决堤洪水,汹涌而出。他哭得浑身发抖,像是要把那些夜晚的恐惧、孤独、自责全部吐出来。
范真真没有劝他别哭,只是轻轻拍着他的背,像母亲哄孩子入睡。
良久,他抬起头,红着眼睛问:“我……以后还能正常吗?”
“当然能。”范真真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而且你会比大多数人更懂得什么是尊严,什么是边界,什么是真正的勇气。这不是诅咒,这是你未来的力量。”
那天傍晚,专项工作组再次启动。根据张浩提供的信息,警方调取了小区监控,发现涉事男子曾在多个深夜单独出入其家中。同时,在恢复手机数据时,技术人员在其微信聊天记录中发现了多段异常对话,包括“小浩真乖”“下次叔叔给你带好吃的”等明显带有诱导性质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通过声纹比对,确认该男子曾在另一起未立案的儿童骚扰案中出现过,地点位于邻市某小学附近。
案件迅速移交检察机关。由于张浩尚未成年且存在二次伤害风险,媒体未公开其身份。但#男孩也会被性侵#话题悄然登上热搜,引发全网讨论。
许多男性网友开始留言分享自己的经历:“初中被表哥摸过,一直以为是自己太敏感”“高中被男老师搂肩膀亲脸,吓得再也不敢去办公室”“我五岁时被邻居老头猥亵,到现在都不敢结婚”。
一位心理学教授发文指出:“男性受害者往往面临更大的社会污名化压力,他们不仅要承受创伤本身,还要对抗‘你应该反抗’‘你不该受害’的刻板印象。这导致绝大多数男性受害者终身沉默。”
范真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常说‘保护女孩’,却很少说‘保护男孩’。可加害者从不分性别选择目标,为什么我们要用性别来定义受害?真正的平等,是承认每一个灵魂都有脆弱的权利,也都拥有呼救的资格。”
一个月后,张浩转入寄宿制学校就读,接受定期心理辅导。他的父母得知真相后震惊不已,母亲连夜赶回,抱着他痛哭:“对不起,妈妈不在你身边……是我们让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
父亲则沉默许久,最终低声说:“爸带你去报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都信你。”
那支记录着他人生第一次勇敢的录音笔,也被送往“百人百声”档案馆。编号:104。
状态:公开共享。
备注:永不删除。
春天到来时,《她说》推出第一百零五期特别节目,《他也说》。节目聚焦男性未成年人性侵议题,邀请三位幸存者以变声方式讲述经历。张浩是其中之一。
他说:“我一直以为,只有女生才会需要帮助……我以为男生就应该打回去……可那时候我才十三岁,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我知道了,不说出口才是最大的失败。录音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证明??我存在过,我受伤过,但我没有消失。”
节目播出当晚,平台新增匿名倾诉量突破五千条,其中男性占比首次超过三成。多地教育局陆续开展“性别中立性教育”试点课程,强调“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任何人都有权拒绝不当接触”。
与此同时,“移动倾听车”项目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新疆喀什站首次设立双语心理咨询通道,帮助维吾尔族少年用母语倾诉;福建泉州站走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为留守儿童提供一对一倾听服务;河北邯郸站则与检察院合作,建立“校园安全哨兵”机制,鼓励学生匿名举报可疑行为。
这些声音不再只是个体的呐喊,而是逐渐织成一张守护之网,覆盖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成人与儿童。
年底,《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正式施行。新增条款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性保护,不得因受害人性别、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影响案件受理与处理进度。”同时设立“未成年人心理救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开展干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