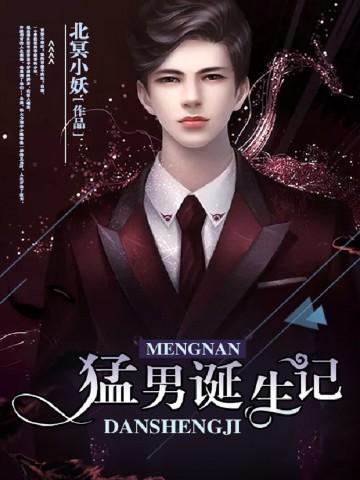我的书库>割鹿记 > 第九百七十七章 拨云渐月明(第3页)
第九百七十七章 拨云渐月明(第3页)
鹿承安仰望着那句话,久久不语。良久,他转身走入新建的灯亭深处,取出一本蒙尘古籍,封面写着《愿学初章》。他轻轻吹去灰尘,翻开第一页,提笔写下序言:
>“吾少时见边民冬夜难归,常冻毙于途,遂立志建灯亭百座,使万里无暗路。
>后遭构陷,身死名裂,然初心未改。
>今幸得少年持灯而来,不问出身,不论过往,唯以光为证。
>故此书重刊,愿天下学子皆知:
>善不必出于圣贤,恶亦非生于天生。
>唯愿长存,灯自可明。”
写罢,他将书置于灯下,任火焰映照字迹。翌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时,数十名流浪学子闻讯赶来,围坐在灯亭外,听一位白发老人讲述“愿”的意义。
消息如风传播,不出十日,岭南各地兴起私塾十余所,皆以“归鹿”为名,教授愿力学说。更有百姓自发清理旧灯亭,重燃灯火。
与此同时,陆昭自归墟归来,已是七日后。他回到愿学堂旧址,只见山谷焕然一新:原本荒芜的土地上,新建了七座环形灯亭,中央立着一块无字碑,碑前插着那柄卢字铁剑,剑穗随风轻摆。
林晚舟迎上来:“我们都等着你。”
“等我做什么?”
“等你开启‘灯会’。”她说,“按照《守灯录》记载,当七灯俱明,七位执灯者齐聚之日,须召开千年未现的‘大愿灯会’,共议天下愿力流转之道。”
牧云也从岭南赶来,带来鹿承安亲笔书信一封,信中只有八字:“愿同燃一灯,不分南北。”
陆昭站在碑前,望着七座灯亭,心中清明如镜。
他拔起卢字铁剑,高举过顶,朗声道:
“以心为引,以愿为薪,以行为火??今召天下执灯者,共赴灯会!”
话音落处,剑尖指向苍穹。
轰隆一声,七座灯亭同时爆发出强烈光芒,光束交汇于空中,形成一座悬浮的巨大灯轮,缓缓旋转,洒下万点星火,落入人间千家万户。
那一夜,无数人梦见自己手持灯火,行走在漫长的道路上,前方虽有风雨,却不再畏惧。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心中有愿,便自有后来者,提灯相迎。
数月后,朝廷派出使者欲封陆昭为“镇国灯师”,却被拒于山门外。使者不解:“如此功绩,为何不受爵?”
守山童子答曰:“先生说,执灯者不当居庙堂,而应在野地。光若只为权贵照亮,便不再是光。”
使者默然离去。
又一年春,东海灯塔迎来新一批守灯人。一名少年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一本泛黄手札,扉页题着《割鹿记补遗》,内文仅有一段:
>“后世若有问:鹿侯究竟善恶几何?
>答曰:他曾点灯,也曾熄灯;
>卢衍斩鹿,亦曾篡史。
>然今有少年持灯而来,不问是非,只问光明。
>是故,不必定论古人,但求不负初心。
>
>割鹿记终,燃灯事始。
>??阿奴绝笔”
少年读罢,望向海天交界处初升的朝阳,轻声念道:“燃灯事始……”
远处海浪拍岸,一如亘古不变的呼吸。
而在大陆最北端的寒狱遗址,积雪之下,一截断裂的鹿角突然微微发光,随即沉寂。
风过无痕,灯影重重。
人未亡,火已燎原。
此灯不灭,自有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