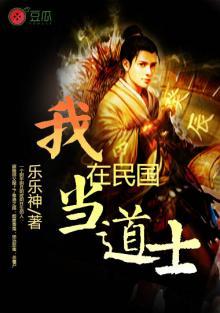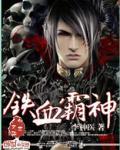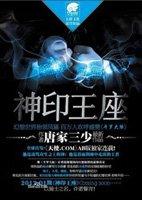我的书库>七零港城杂事 > 126第 126 章(第3页)
126第 126 章(第3页)
下一瞬,第七窑窑门自动开启。
浓雾弥漫中,一道身影缓步走出。
是杨阿土。
但他变了。
他的双眼泛着淡淡的金光,行走时脚步无声,仿佛踩在另一个维度之上。他手中捧着一只全新的素胎小盏,盏身尚未施釉,却已浮现出复杂纹路??那是《天工篇》全文,一笔一划,宛若天生。
“我见到了他。”他开口,声音叠着双重回响,像是两个人同时在说话,“他也见到了你们的努力。他说……第八位守器者,不必等人来选,只需自己迈出那一步。”
话音落下,他将小盏高举过头。
刹那间,七地窑火齐齐暴涨,天空雷鸣滚滚,第一滴雨水终于落下。
这场雨,覆盖了七大窑址方圆百里,持续整整一夜。气象局数据显示,降雨成分中含有大量稀有矿物离子,与窑炉排放物高度吻合,却无任何污染残留。生态专家惊呼:这片区域的土壤活性提升了%,植物生长速度加快近三倍。
舆论彻底反转。
“非遗科技联动”从嘲讽变为热议,#让瓷器改变世界#话题阅读量突破五十亿。无数青年报名参加“民间窑火复兴培训营”,全国各地废弃古窑陆续被修复启用。
而那位藏身科学院的“第六人”,在“净穹工程”即将启动前最后一刻,主动辞职消失。只留下一封匿名信,交给了国家文物局:
>“我曾以为,阻止你们是对文明负责。但现在我明白,真正的危险,不是火太旺,而是人心太冷。我不再阻拦。但我也无法同行。请原谅一个老者的怯懦。”
三个月后,清明前夕。
联合国正式批准“全球窑脉复兴计划”为跨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七位承志者受邀赴日内瓦演讲,介绍“窑火气候调节机制”。会场上,单水儿展示了那枚来自1954年的铜铃,当她轻轻摇动,全场灯光忽明忽暗,仿佛回应某种古老频率。
归途中,她在机场候机厅停下脚步。
那个背着陶艺包的年轻人就坐在角落,低头画着什么。她走近一看,竟是第七窑的结构图,精细到每一根通风管道的位置。
“你是谁?”她问。
年轻人抬头微笑,拉开衣领??一朵半开的莲花刺绣赫然显现。
“我叫林知微。”他说,“我母亲临终前说,我父亲留给我的名字,不该埋在土里。”
单水儿怔住。
风铃又响了。
这一次,是从她自己的口袋里。
她掏出那枚铜铃,发现表面已完全开片,裂纹组成了一幅微型星图,指向北方某处荒原??那里,曾有一座从未被记载的窑址,在史书中被称为“归墟之炉”。
她笑了。
转身对众人说:“走吧,还有最后一座窑等着我们。”
山谷之外,春风拂过新绿的茶园,窑烟袅袅升起,如丝如缕,织成一片看不见的网,温柔地包裹着这个仍在失衡边缘挣扎的世界。
而在地球另一端,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正盯着一份异常报告:臭氧层空洞扩张趋势,首次出现逆转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