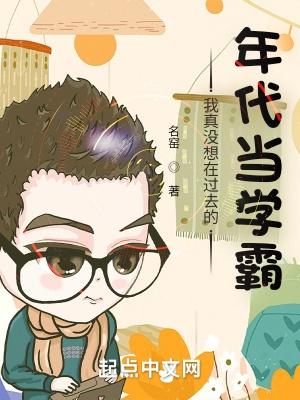我的书库>魏晋不服周 > 第193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第3页)
第193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第3页)
而此时,江南已悄然完成一场静默革命。
全国年报汇总出炉:耕地面积较十年前增长四成,人口回升至两千三百万,太学附属小学达一千二百所,基层医馆覆盖八成乡村,犯罪率下降七成。更令人振奋的是,百姓对朝廷的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高达八成五,远超东晋初年。
袁熙站在建康城楼上,手握最新一期《民生通报》,久久不语。
身后,李知微轻声问:“接下来呢?”
袁熙转身,望向北方苍茫大地:“接下来,我们要让北方的孩子也念上书。”
******
永康十年夏,袁熙亲率五百文官、千名教师、三百医者组成“北行团”,穿越战火,进入收复区。他们在废墟上搭起帐篷,升起第一面写着“义务教学”的旗帜。没有桌椅,就用砖头垒台;没有课本,就手抄《识字篇》;没有药品,便采集中草药熬制汤剂。
每到一地,袁熙必亲自主持“立信仪式”:当众宣读《治理律》,焚烧旧日苛捐杂税名册,发放种子与农具,并郑重承诺:“从此以后,你们不是谁的奴仆,而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有个小女孩问他:“叔叔,我们真的能上学吗?我娘说,女孩子读书会招灾。”
袁熙蹲下身,从行囊中取出一支铅笔和一本练习册,轻轻放在她手中:“拿着。这支笔比刀剑厉害,它能让你看见整个世界。”
女孩怔住,继而泪流满面。
******
五年后,北方七州基本平定。
赵固解甲归田,自称“老兵”,隐居莲塘里畔,每日帮孩童劈柴挑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征战,不及袁公一纸文书得民心。”
李知微出任首任“国民教育卿”,主持编纂《中华通识教材》,确立“人人皆应受教育”为国策。
陈阿六则带着一群退伍老兵,在边境地带组建“屯垦兵团”,一边开荒种地,一边训练青年防卫国土,被称为“不穿铠甲的长城”。
而袁熙,始终未曾停下脚步。
六十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巡视北方边陲。雪落满肩,步履蹒跚。随从劝他乘轿,他摆手拒绝:“百姓走过的路,我也该走一遍。”
抵达一处新建村落时,孩子们围上来,齐声背诵《识字篇》第一章:“天地初开,万物有序。人生于世,皆有尊严。不论男女,不分贵贱,皆可读书,皆应守法……”
袁熙听着,忽然笑了,眼角泛出泪光。
当晚宿于村塾,他提笔欲写日记,却发现墨尽。学生连忙递来砚台与清水,他摇摇头,掬起一捧雪化于碗中,磨开残墨,颤抖着写下最后几行:
“余一生所求,非功名,非富贵,惟愿天下无饥寒之家,无失学之童,无含冤之民。今见稚子诵书声起于荒原,知春雷已动,种子破土。此身虽朽,此志不灭。
文明如种,深埋于土,静待春雷。我不过是个浇水的人。
然,水既已浇,何惧岁月漫长?”
次日清晨,村民发现塾屋门未锁,袁熙端坐灯下,手握毛笔,头微垂,呼吸已止。
窗外,大雪初霁,朝阳升起,映照千里沃野,一片银白如新。
人们说,那天早上,最先醒来的是学堂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