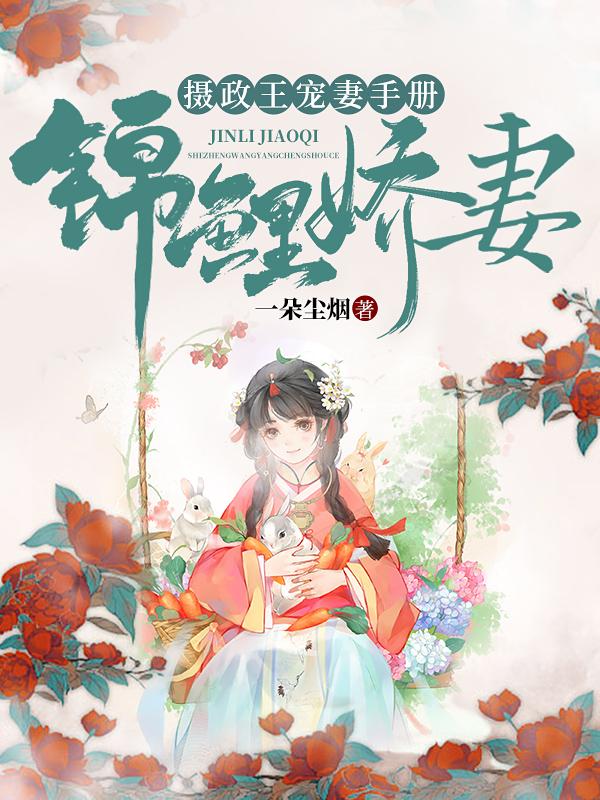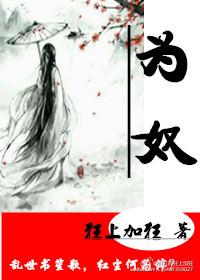我的书库>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35章 本王请你别走留下来(第4页)
第635章 本王请你别走留下来(第4页)
多年过去,明烛书院声名远播,学子遍及天下。许多人慕名而来,只为见一眼那位白衣素发、额间银痕如星的女子。但她从不接受供奉,只坚持授课育人,尤其重视“守夜人文史课”。
某年冬至,一位年轻女官前来拜访,自称曾在宫中整理旧档时,发现一份密诏:当年太后并非完全受控于灵素,而是早知双生命格,却因私欲隐瞒真相,甚至暗中推动轮回延续,只为保全皇权正统。
“她以为掌控命运就能永享尊荣。”女官叹息,“结果呢?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她。”
念烛听罢,只说了一句:“权力若不配以慈悲,终将反噬其主。”
次日清晨,她在课堂上新增一节:“**历史的背面**”。
讲的是那些被掩盖的真相,被抹去的名字,以及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如何改变时代洪流。
她说:“不要只看胜利者写的史书。真正的光,往往藏在失败者的墓碑上。”
又是一年清明。
渔夫们照例在慈幼堂遗址摆放蓝花,却发现今年多了些不同??七个孩子各自带来一首诗,贴在废墟残墙上。其中阿星的那一首最为动人:
>昔有姐妹分两途,
>一生负剑一生哭。
>今日我辈执笔立,
>不写悲歌写归途。
>若问前尘何以解?
>心中有灯即是路。
风吹纸页,沙沙作响,仿佛回应。
而在极北考古现场,那位老渔夫的儿子拾起一块新出土的陶片,上面刻着半句模糊文字:
>**“守夜者,非战而胜,因心不死。”**
他不懂其意,随手交给学者。学者摇头:“又是些荒诞传说罢了。”
可就在这瞬间,远处灯塔的光芒恰好扫过荒原,照亮了那行字。
那一刻,风停了,沙落了,时间仿佛也为之静止。
而在孤岛灯塔之上,念烛依旧每日登顶巡视。她不再梦见战火,也不再听见低语。胸口的暖意始终存在,温和而坚定。
有时,她会取出阿烛的军刀,轻轻擦拭,然后放回原处。
她知道,姐姐从未离开。
因为她早已成为那盏灯本身??不必耀眼,不必永恒,只需在每一个需要的夜晚,静静燃烧。
某夜,她倚栏望月,忽见海面泛起涟漪,一艘陌生小船缓缓靠近。船上无人,唯有甲板中央摆着一本崭新的空白册子,封面洁白如雪,封底烫金三字:
**《守夜录》**
念烛拾起它,翻开第一页,提笔写下第一行字:
>“此录始于光明觉醒之日,记凡人如何以心火照亮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