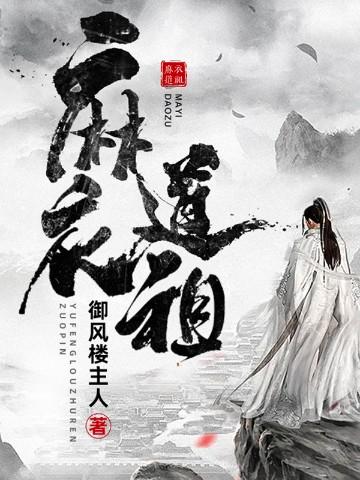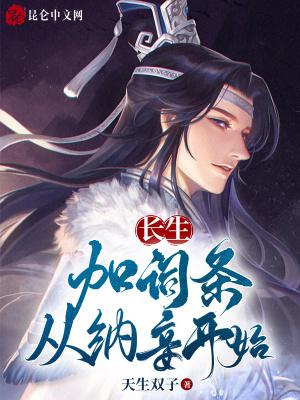我的书库>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大早就来(第3页)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大早就来(第3页)
全国腐败率下降七成二,诉讼积压减少九成,税收连续三年稳步增长。更令人欣喜的是,民间读书风气大变。以往孩童背诵八股只为功名,如今乡间私塾纷纷增设算术、律法、农政课程。有老塾师感慨:“以前教学生写‘子曰诗云’,现在还得讲‘如何计算亩产’‘怎样分辨契约真伪’。”
科举考场外,不再只见愁眉苦脸的书生,更多青年手持实务笔记,相互讨论“灾年借贷利率是否应设上限”“河道治理经费如何分摊”。
甚至有女子化名男子参加考试,虽最终被查出身份取消资格,但舆论一片声援。《明政公报》发表社论:“若女子之才胜于男子,何以不得为民服务?请陛下考虑开设女科。”
朱元璋看后未置可否,却悄悄下令在公主府学堂增设“女子行政班”,毕业后授予“参事”衔,可入各部观政学习。
李可得知,欣慰一笑:“种子,终于发芽了。”
这一年冬,李可再度入宫述职。
朱元璋已年过六旬,鬓发尽白,但仍精神矍铄。他拉着李可的手,走到御花园湖畔,指着冰面上一群嬉戏孩童:“你看,那些孩子长大后,或许也会考科举、做官。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一边杀人一边悔恨。他们会知道,官不是骑在百姓头上的老爷,而是扛着百姓往前走的挑夫。”
李可轻声道:“只要制度不变,这样的挑夫,就会一代接一代。”
朱元璋忽然问:“你说,要是有一天,我也成了阻碍新政的人,你会怎么办?”
李可毫不迟疑:“我会劝您。若劝不动,就辞职归田。若您执意废除新政,那我就写一本书,告诉后人,曾经有过一场光明,是如何被熄灭的。”
朱元璋愣住,随即仰天大笑:“好!这才是朕的李可!”
笑声惊起飞鸟,掠过湖面,投下碎影斑驳。
数月后,李可辞去中枢要职,自愿赴云南边陲任布政使参议。众人不解,问他为何放弃高位远走蛮荒。
他在离京当日答道:“新政已在中枢扎根,我不在,也能运转。但边地依旧闭塞,贪官横行,百姓视官如虎。我要去那里,让最后一个角落的人也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愿意低头听他们说话的官。”
临行前夜,朱元璋亲赐金杯一盏,杯身镌刻四字:“天下清名”。
李可叩首受之,泪流满面。
三年后,云南政风焕然一新。李可主持修建水利十三处,裁撤冗吏二百余人,创办“边民讲习所”,教土司子弟识字明理。当地夷民感其德,尊称“李阿爸”,每逢节日焚香祭拜。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
临终前,他留下遗诏:“凡我子孙,若有敢废除高薪养廉、审计公开、连坐追责三项制度者,不承认其为朱氏血脉,天下共击之。”
建文帝继位,首道诏令便是迎李可回京,拜为太子太傅,总领新政监督事务。
李可归来之日,应天万人空巷。百姓夹道相迎,有人跪地磕头,有人高呼“活佛降临”。他坐在马车上,看着熟悉的街景,听着熟悉的乡音,忽然觉得这一生从未如此踏实。
当晚,他独自登上钟楼,俯瞰万家灯火。
风很大,吹动他的白发与衣袍。
他低声念道:“我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个不愿再看着百姓流泪的普通人。若这世上有神明,我希望?听见??请让清明延续,请让希望不灭,请让每一个想做好官的人,都不再孤独。”
远处,报馆灯火依旧明亮,《明政公报》正在赶印明日头条:
**《洪武新政十周年纪实:从“狗都不当”的官,到万人敬仰的职业》**
标题之下,是一幅画像:一位身穿七品官服的男子,蹲在田埂上,握着老农粗糙的手,认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