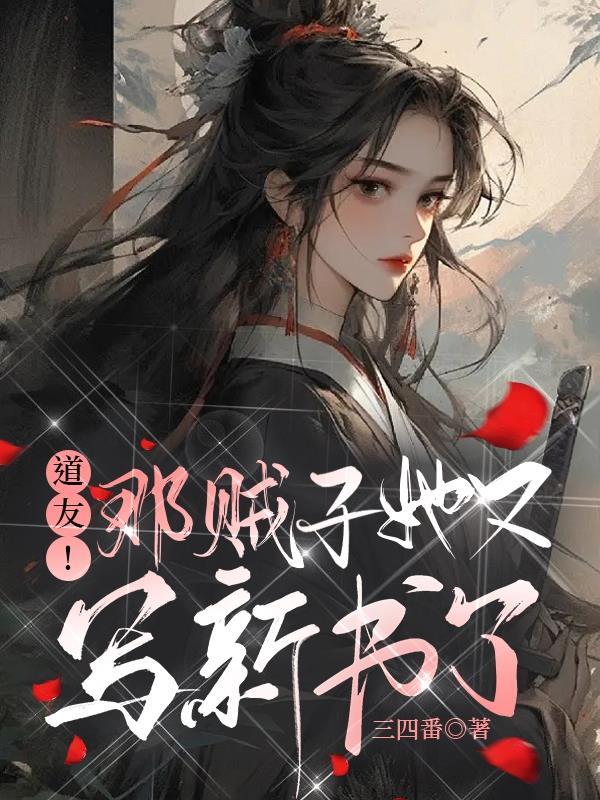我的书库>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一百八十四章 你的意思你要祸害我大明的新一代(第2页)
第一百八十四章 你的意思你要祸害我大明的新一代(第2页)
满殿寂然。户部尚书垂首不语。
最终,建文帝下旨:周廷章革职拿问,抄没家产,三族监禁待审;永平布政使等地方官员一律削籍流放;涉案商人全部缉拿,财产充公。同时颁布新规:今后凡涉及民生钱粮之案,无论品级高低,七日内必须立案,三个月内结案公示,逾期者主审官连坐。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百姓奔走相告,称“天理尚存”。而与此同时,一股暗流也在悄然涌动。
五月十五,端午前夕。李可在家中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藏于一只咸鸭蛋中,经化验确认无毒。拆开一看,只有寥寥数语:“七月七,天河开,旧宫灯,照幽台。”
他盯着这十二个字良久,忽然脸色大变,唤来陆昭:“快查宫中灯具更换记录!尤其是太庙和内廷偏殿!”
陆昭不解:“为何查灯?”
“这是密语。”李可沉声道,“‘天河开’指七夕之夜星河横贯,‘旧宫灯’暗示前朝遗物,‘幽台’则是洪武年间一处秘密地牢的代号,位于皇城西北角,现已封死。有人要用这个时间、这件信物,开启那个地方??那里藏着太祖皇帝亲手焚毁的一批宗室密档,记载着诸王早年谋逆证据。若被人抢先取出,嫁祸朝廷,必将引发宗室集体反扑!”
陆昭立即调集亲信,彻查宫中灯具。果然发现,三日前有两名工匠奉“修缮旧殿”之命进入内廷,更换了一批铜制莲花灯,而这些灯的底座纹路与洪武旧制完全一致,极可能藏有机关。
当夜,陆昭带人突袭工匠住所,搜出地图一张,标注了通往幽台的地底暗道入口,位置正在御花园假山之下。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名工匠竟是燕王旧部,三年前伪装成平民混入工部服役。
李可当机立断:“封锁御花园,掘开封土,派人日夜值守。同时通知建文帝,加强皇宫守卫,暂停一切非必要修缮工程。”
七月初六,夜雨倾盆。李可独坐书房,翻阅《官鉴录》手稿修订版。窗外雷声滚滚,仿佛天地怒吼。忽然,一道闪电照亮庭院,他看见墙角闪过一人黑影,手持短刃,正攀向屋顶。
他不动声色,吹灭烛火,悄然取出床下铁尺。片刻后,刺客破窗而入,挥刀直扑床榻??却劈了个空。李可从梁后跃下,一记扫腿将其掀翻,铁尺压喉,厉声喝问:“谁派你来的?”
刺客咬牙不语,嘴角忽现黑血??已服毒自尽。
陆昭随后赶到,查验尸体,发现其腰间藏有一枚青铜令牌,刻着“龙渊”二字。
“龙渊卫?”陆昭倒吸一口冷气,“那是洪武初年设立的秘密护卫,专司监视藩王,后因权力过大被裁撤。难道……有人重建了它?”
李可冷冷道:“不是重建,是一直存在。只是换了名字,换了主人。这股力量从未消失,它蛰伏在体制缝隙中,等待时机反扑。今日刺我,明日便可刺帝。”
次日清晨,李可入宫面圣。建文帝神色憔悴,昨夜亦遭刺客袭击,幸有贴身太监舍身相护。二人相对无言,唯有痛楚与愤怒交织。
“老师,我们该怎么办?”建文帝终于开口,“若连皇宫都不安全,还谈何治国?”
李可深吸一口气:“只有一个办法??把所有的暗处,全都曝晒在阳光下。”
他提出三项举措:第一,在全国推行“官员财产公示令”,凡五品以上官员,须公开三代直系亲属田产、商铺、借贷情况,违者立即免职;第二,建立“百姓观政团”,每州选派十名平民代表,轮流进京旁听六部会议,有权质询政策执行;第三,重启“凤鸣计划”升级版,赋予巡按御史临时拘捕权,遇重大腐败或谋逆嫌疑,可先控制相关人员,再上报备案。
建文帝犹豫:“此举前所未有,恐被斥为‘威权过度’。”
李可直视其目:“陛下,您想要一个表面太平、实则腐烂的王朝,还是一个虽有争议、但民心尚存的江山?”
七夕当晚,暴雨如注。李可率百名巡按御史集结于午门外,宣读新令全文。数千百姓冒雨围观,有人高呼:“李大人万岁!”他挥手制止,只说一句:“我不是万岁,我只是不愿再让百姓流泪的普通人。”
凌晨时分,第一批财产公示名单张贴于各大衙门前。榜首赫然是前内阁大学士之子,名下拥有良田八万亩、当铺十七家、海外商船三艘,远超其父一生俸禄总和。民众哗然,要求严查之声席卷全城。
与此同时,幽台密档终被找到,但已被焚毁大半。残卷中仍有片段提及秦王、晋王早年勾结蒙古意图叛乱,证据确凿。建文帝下令密封保存,严禁外泄,仅作为震慑宗室之用。
七月十八,周廷章伏诛于西市。行刑前,他在囚车上大声忏悔:“吾非不知法度森严,然见他人贪而无事,遂心存侥幸……今日方知,天网恢恢,不在早晚,而在人心未死。”
李可站在远处观望,未发一言。归途遇雨,他索性收伞,任雨水打湿全身。回到家中,取出那封牛三娃的来信,轻轻抚过纸面,喃喃道:“你们相信好人能赢……可好人,也要活得够久才行啊。”
冬至那天,京城飘起第一场雪。李可病倒了,高烧不退。医生说是积劳成疾,需静养百日。但他仍在床上批阅公文,口述奏对。周怀礼从贵州归来,带来好消息:当地苗民自发立碑,上书“李公渠”,纪念当年他主持修建的引水工程;女子参事班毕业六人,已有两人出任县丞,主管赋税与司法。
“老师,新政真的扎根了。”周怀礼哽咽道,“不只是制度,是人心变了。”
李可微微一笑,望向窗外纷飞白雪:“那就继续守下去。一代人做不完的事,就交给下一代。只要每年都有年轻人问‘做官能不能像李大人那样’,我们就没输。”
腊月廿三,小年。宫中送来御赐药膳与貂裘,附建文帝亲笔信:“朕愿以江山为誓,不负先生半生肝胆。”
李可提笔回复,仅八字:“但求无愧,何须铭记。”
翌日清晨,阳光破云而出,洒在应天府衙前的政务公开榜上。新的一榜刚刚张贴,内容是关于明年水利建设预算的详细分配。一群孩童围拢过来,踮脚念着上面的文字,一字一句,清晰响亮。
李可拄杖立于人群之后,静静听着。风吹动他的白发,也吹动榜纸哗啦作响,如同岁月深处传来的回音??那是千万百姓共同诵读正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