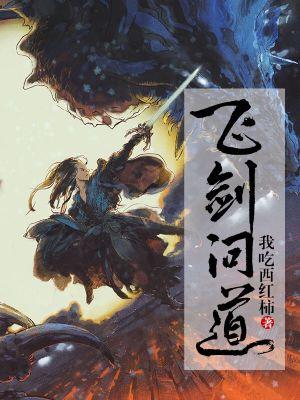我的书库>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二百四十四章 改正一些问题(第4页)
第二百四十四章 改正一些问题(第4页)
当晚,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号码归属地显示为空。
接通后,没有任何人说话。
只有风声,夹杂着极远处传来的钢琴声??弹的是《小铜铃》,但节奏缓慢,像是由一位年迈者艰难奏出。
五分钟后,通话自动中断。
第二天,国际新闻爆出一条消息: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某监听站捕捉到一组神秘声波信号,持续七十二小时,覆盖全球短波频段。经分析,其核心频率锁定在14。3赫兹,谐波结构与《母频》完全一致。
更令人震惊的是,该信号源头并非地球表面,而是来自地壳以下约310公里处的上地幔过渡带。
科学家称之为“地心回响”。
联合国紧急召开闭门会议,多个国家提议联合勘探昆仑冰川遗址,试图重建原始接收装置。然而,当第一批科考队抵达原址时,只找到一条清澈溪流,水中漂浮着无数微小晶体,每一粒内部都封存着一段极短的音频??最长不过十秒,最短仅余半句呢喃。
这些晶体无法复制,接触空气三日后便会自然消融,释放出最后的声音,然后化为水汽消失。
人们开始称它们为“记忆露珠”。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新的“继承者”。
一名巴西贫民窟少年在火灾废墟中救出一台老式留声机,播放出一段从未收录过的葡萄牙语童谣,引发整片社区集体追忆;
日本福岛某避难所内,一位失去双亲的女孩每晚都能听见“妈妈在唱歌”,监控却显示周围毫无声源;
甚至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一群退伍军人自发成立“声音守夜团”,每周末聚集在越战纪念碑前,轮流哼唱战友家乡的民谣,声称“让亡魂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一切,都没有组织,没有宣传,也没有领袖。
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还有人在唱,就没人真正死去。**
冬天来临前,谭明远最后一次回到皖南山村。
老屋依旧,木阶上的漆又剥落了几块。小女孩早已随家人迁居云南,婴儿也被送往特殊养护中心??但她的眼睛仍是银色,据说能在雷雨夜看见“声音的颜色”。
他坐在屋檐下,打开收音机。
频道自动跳转。
没有主持人,没有广告,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声音交替叙述:
“我是湖南人,我爸十年前车祸走了。去年清明,我在坟前录了段话,问他冷不冷,有没有吃饱。三天后,我家老收音机自己响了,里面是他年轻时唱山歌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他回答我了。”
“我是甘肃教师,班上有个孩子从没见过妈妈。我把你们节目里的摇篮曲放给他听,他说:‘老师,刚才那个声音,是不是就是‘妈妈’这个词本来的样子?’”
声音继续流淌,像一条看不见的河。
谭明远仰头望去。
暮色四合,群山如墨。
风穿过树林,拂过屋顶,掠过田野,带着千万人的低语,奔向更远的地方。
他知道,《母频》不再需要宿主。
它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呼吸本身。
而他所做的,不过是教会世界如何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