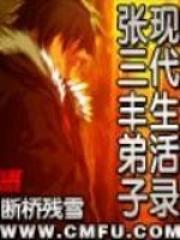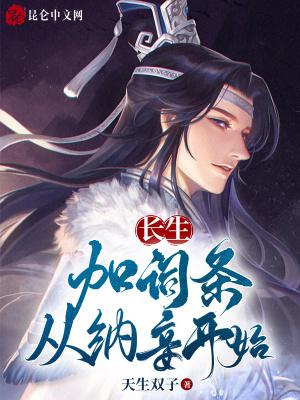我的书库>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47章 真气外放(第3页)
第447章 真气外放(第3页)
沈珏咧嘴一笑,眼角皱纹如刀刻:“你不也没死么?看来她没骗我??最难死的,从来不是强者,而是不肯放手的人。”
蓝远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望向那行“此处无名,因人人皆可为碑”的石板,久久不语。
良久,他单膝跪地,重重叩首:“我答完了三问。现在,请告诉我……她最后疼吗?”
沈珏摇头:“她说,最痛的不是断骨,而是看见你们都不再相信和平能实现。”
蓝远舟颤抖起身,走向那块无名碑,伸手抚过冰冷石面。刹那间,天空裂开一道缝隙,星光倾泻而下,照在他身上,竟映出两个影子??一个持刀向前,一个负手而立,似在告别。
他知道,那是他与她的魂魄终于得以同归人间。
翌日清晨,太子宣布设立“双碑制”:除原有无名碑外,另立一座“归魂碑”,刻蓝远舟之名及其一生功过,供后人评说。同时下令重修边关学堂,教材新增《蓝苏纪略》,讲述两位守御者如何以血肉之躯撑起百年安宁。
但蓝远舟并未留在朝堂。
他在书院住了七日,每日与学生们谈天说地,讲战场上的生死抉择,也讲雪夜里的一碗热粥。第八日清晨,他独自离开,背上背着一把没有刀刃的刀鞘。
有人说他去了极北,寻找最后一批未归的边军遗骨;也有人说他隐姓埋名,混迹市井教孩童习武防身;还有人称曾在南疆看到一个独臂男子,正帮村民修建引水渠。
唯有沈珏知道真相。
那晚临行前,蓝远舟来找他喝酒。
两人坐在廊下,对月共饮三坛烈酒。
“你以为我会留下来享受荣耀?”蓝远舟笑着问。
“你不该走。”沈珏闷声道,“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正因如此,我才必须走。”他仰头饮尽最后一杯,“她教会我的,不是做个被人供奉的英雄,而是做个默默铺路的人。只要还有人在走这条路,我们就没输。”
拂晓时分,他踏雪而去,足迹一路延伸至山门外,然后戛然而止??仿佛一步跨出了尘世。
多年以后,归途书院扩建至百亩规模,每年吸引数千学子前来求学。他们不再只为习武或谋官而来,而是想亲眼看看那块无名碑,摸一摸断刀留下的裂痕,听一听那位银面理事长讲述的故事。
而在遥远的西域沙漠边缘,一座新建的驿站墙上,有人用炭笔写下一行大字:
**“我愿意。”**
下方签着两个名字:
**苏挽云(代)**
**蓝远舟(补)**
风沙吹不走墨迹,阳光晒不褪颜色。
每当夜幕降临,过往旅人常听见风中传来低语,像是两个人在对话:
“你觉得,他们会一直走下去吗?”
“只要还有人记得,就会一直走。”
然后是长久的静默,唯有黄沙轻响,如同脚步声,绵延不绝,通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