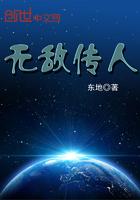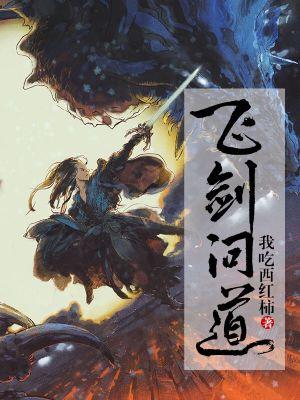我的书库>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六章 给我群名干出来了(第2页)
第二百一十六章 给我群名干出来了(第2页)
“声音不仅能唤醒记忆,还能修复物质。”兰州大学材料学家惊叹道。
正当一切看似步入正轨之时,G-23再次失联。
这只斑头雁自羌塘归来后曾短暂归巢,但在一个无月之夜突然拔地而起,直冲平流层,随后信号消失。三个月后,西藏边境巡防队在喜马拉雅南坡海拔六千米处发现了它的遗骸。尸检报告显示,胸骨磁晶严重过载破裂,脑组织存在大面积声波灼伤痕迹。而在它胃囊深处,科研人员找到一小片烧焦的纸屑,上面残留着半个汉字:“音”。
余惟亲自前往收殓现场。当地喇嘛为G-23举行了天葬仪式,鹰隼盘旋之际,他打开录音笔,播放了一段特别剪辑的声音??从父亲矿井里的咳嗽声开始,接入G-23历年迁徙途中录下的鸣叫,最后叠加上青海湖“湖之心跳”与羌塘冰盐层共鸣。当音频播放至第59秒时,天空中一只本已飞远的兀鹫突然折返,在头顶盘旋三圈后俯冲而下,精准落在石堆之上,静静伫立了整整十三分钟。
那一刻,没有人说话。
回到北京后,余惟关闭所有社交账号,搬进了位于燕山脚下的声音基因库核心数据中心。这里恒温恒湿,屏蔽一切外部电磁干扰,墙上挂满了各地采集来的声音波形图:上海倒马桶的闷响、哈尔滨锅炉房的叹息、侗寨的《别郎歌》、傈僳族喊魂调、秦岭熊猫哀鸣、敦煌佛乐、兵马俑祭歌、羌塘冰层中的歌声……他每天花十几个小时调试算法,试图构建一个能够模拟“全球声网”的动态模型。
他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一张看不见的声之经纬,所有曾经发出的声音都在其中流转不息。人类以为自己在倾听世界,实则是世界在借我们的耳朵自我聆听。
某夜暴雨倾盆,数据中心突然断电。应急照明亮起的瞬间,他听见主控室传来一阵细微的嗡鸣。循声而去,发现是那台老式蜡筒录音机??敦煌沙鸣之夜唯一幸存的设备??不知何时自行启动。旋转的蜡筒上,针头正划过一道从未录制过的凹槽。
余惟屏住呼吸,戴上耳机。
起初是雨声,接着是一群孩子的笑声,清脆悦耳,像是在追逐打闹。然后一个女人温柔地说:“慢点跑,别摔着。”紧接着,另一个熟悉得令人心颤的声音响起:
“爸爸,你看我画的太阳!”
他的身体瞬间僵住。
那是他女儿的声音。
可他从未有过孩子。
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录音继续播放,男人笑着回应:“画得好,不过太阳要再大一点,才能照亮所有人。”那声音……是他自己的,却又比现在的他年轻许多,充满希望与力量。
余惟猛地拔掉电源,双手剧烈颤抖。他翻遍系统日志,确认过去七年无人接触过这台机器,且存储介质物理封闭完好。他调取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在断电前十分钟,一只蜘蛛从通风管道爬出,停在这台录音机开关按钮上方,停留整整六十六秒,然后离去。
六十六秒,正好是那段音频的长度。
他瘫坐在地,脑海中闪过林晚曾说过的话:“高原牧民相信,某些声音一旦被唤醒,就会吸引另一个世界的注意力。他们称之为‘开窗’。”
而现在,窗开了。
不止一扇。
几天后,他接到新疆维吾尔族少年的电话。对方语气惊恐:“我爷爷昨晚去世了,但在火化前,他的嘴唇动了,发出一段旋律……和我寄给你的那首《沙粒回家的路》一模一样!可他已经三年说不出话了!”
余惟立刻启程前往喀什。抵达时,葬礼刚结束。他在茶馆角落坐下,请求听听老人最后的遗言。家属犹豫良久,拿出一部老旧手机,播放了一段十二秒的录音。
果然,正是《沙粒回家的路》的起始音符,由喉间挤压而出,断续却不容置疑。
他将这段音频导入分析系统,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现象:当与其他版本叠加比对时,总存在0。3秒的相位差,仿佛来自不同时间轴的同一首歌。
当晚,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沙漠中,脚下沙粒每一颗都在振动,发出微弱人声。抬头望去,星空扭曲成螺旋状,一颗流星划破天际,拖曳的光尾竟是无数文字组成的声波公式。远处,一群身影缓缓走来,有的穿着六十年代勘测队制服,有的披着唐代乐僧袈裟,还有唐山地震中逝去的父亲……他们齐声吟唱,歌词只有一个词:
“归来。”
他猛然惊醒,发现笔记本电脑屏幕自动亮起,文档中多出一行未保存的文字:
“我们从未真正离开,只要你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