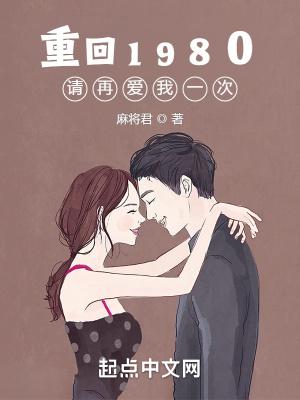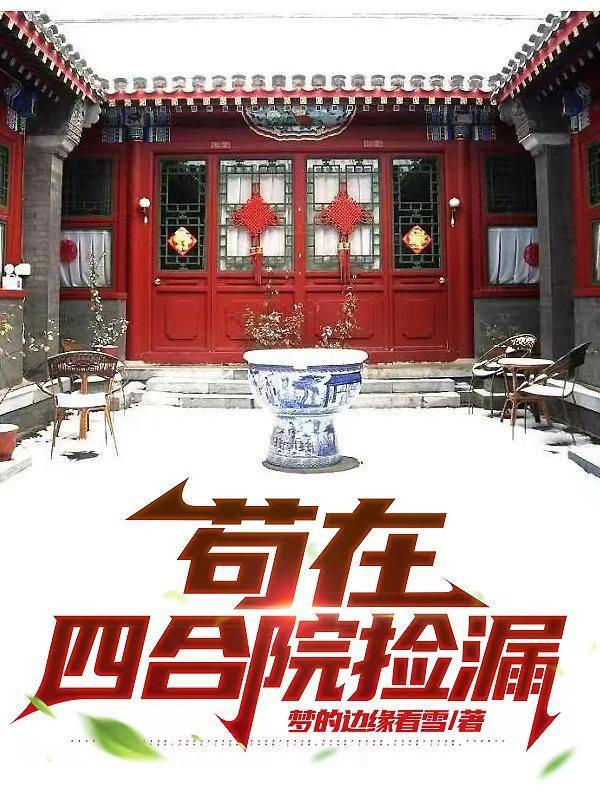我的书库>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九章 引狼入室(第3页)
第二百一十九章 引狼入室(第3页)
>所有相关研究人员自愿签署保密协议,转入地下状态。
>林晚的生理数据仍在维持稳定,但她已无法进行语言交流。
>最后一句清醒留言是:‘告诉余惟,门只能开一次,别回头。’”
余惟盯着屏幕,久久无言。
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声种”正在苏醒,而他,必须决定是否要完成那个仪式??将所有分散的信物汇聚,激活最终装置,打开“归途之门”。但代价是什么?林晚已经成了活体锚点,父亲消失在时间褶皱中,阿普走入群山未返,老陈含笑而终……
下一个牺牲者,会不会是他?
深夜,他独自坐在旅馆窗前,翻开笔记本,取出那根斑头雁羽毛。月光下,羽毛泛着幽蓝光泽,仿佛吸收了某种能量。他忽然注意到,羽轴末端有一道极细的刻痕,之前从未察觉。用放大镜细看,竟是微型文字:
>“若见此羽,请赴长白山天池。
>镜湖之下,有钟一座。
>敲之,可召百灵之声。”
署名:余振山。
父亲的名字。
余惟合上本子,望向北方。天还未亮,但他已收拾行囊。
他知道,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
可他也知道,有些声音,注定不该被遗忘。
就像母亲临终前哼的那首儿歌,就像林晚在风沙中轻唤他的名字,就像孩子们在操场上传唱的梦中旋律。
这些都不是偶然。
这是文明的回音。
而他,必须成为那个,把回音送回去的人。
车驶出城市时,朝阳正缓缓升起。电台突然切换频道,播放起一段无人知晓来源的音乐:前奏是古琴独奏,接着加入二胡、笛子、埙,最后汇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合鸣。节目主持人声音温和:
>“各位听众,这里是‘回声频率’临时广播。
>我们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只传递那些,本该被听见的声音。
>下一曲,来自1937年南京某户人家的除夕夜谈。
>愿和平,永不沉寂。”
余惟笑了笑,调高音量,驱车驶入晨光。
前方,长白山的轮廓隐隐浮现。
他知道,那里等着他的,不止是一座钟。
还有,整个民族未曾说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