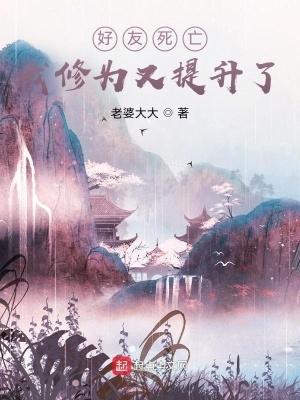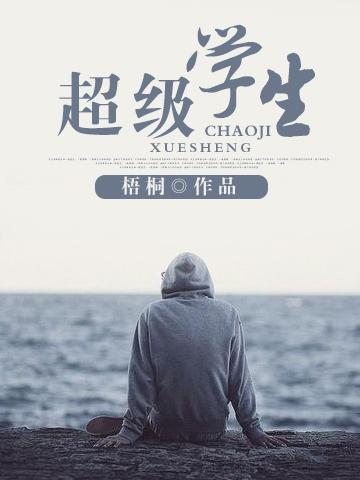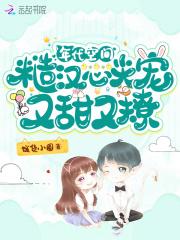我的书库>汴京食滋味 > 3540(第3页)
3540(第3页)
江知味不敢耽搁,都是鲜食,快刀斩乱麻地做了才是头等的要紧事。
灶房中生起柴火,哗的一声响,雪白的牛乳先下了锅。
这牛乳是从水牛身上现挤的,闻着奶香扑鼻,新鲜又热乎。那挤奶的妇人说可以直接喝,但江知味没敢,怕生牛乳会喝出什么毛病来,还是煮过后稳妥。
一旁剁姜末,用纱布包着,研出姜汁倒在碗中。
煮开的牛乳用井水镇一镇,还温热的那些,放在海碗里高高举起,如飞瀑那般哗啦啦地冲到姜汁里。
此为姜撞奶。
余下的那些继续放凉。江知味挑出几碗,将碗中结出的乳黄色奶皮用筷子刮下来送到嘴里。品啜一番,嗯……奶味浓得不行,香得直糊喉咙。
至于尚留有奶皮的那几个碗,轻轻顺着碗边,将里头的牛乳倒入打好的蛋清中,过筛,再倒回盛有奶皮的碗中,镇以井水,等待它变得冰凉,就成了双皮奶。
被吃掉奶皮的牛乳则被放至温凉,加米酒汁搅至均匀,上锅蒸个一刻钟,再隔水冰镇,直至凝固,便成了冰酥酪。
一奶三吃,今日大家伙儿可有口福了。可惜都不能立马开动,等待的工夫,正好把辣卤鹌鹑给解决了。
早前王掌柜那边的香料都已经送来了。之所以当初未雨绸缪,就是为接下来要推出的辣卤做准备。
卤味这东西,无论是在后世还是在而今的大宋都很吃得开。
尤其是在这个盛行吃爊肉的朝代,卤味的做法与其相近,相当于在爊肉的基础上再行改良,取的正是摆摊秘诀中“人有我优”的道理,也更容易被当地的老百姓接受。
江知味做的卤水,用的是专门的商用配方。自家吃个卤味,挑拣些爱吃的鸡爪子、鸭脖子,放个卤料包、添点儿生抽、老抽,小火慢卤就成。
商用的却更麻烦些。
像今日要做的辣卤鹌鹑,就得先把鹌鹑在红曲水里上个色,下油锅炸至金黄。捞出控油,制卤水、熬糖色。
卤水里用到的香料共计十八味。姜片、大葱、芫荽、茱萸、各类香料先过油炸,还不能直接下清水,要想那鹌鹑风味绝佳,得用猪大骨或者鸡架子熬出的高汤。
鸡架难寻,猪骨却能从钱屠那儿轻易搞到。敲碎的猪骨加黄酒、十三香、葱姜,从晨起小火熬到这会子火候刚好。
再将高汤与那炸好的油料一拌,加干茱萸、干花椒和调味的盐、糖、作味精用的干香蕈粉,小火卤制两刻钟,浸泡个一刻钟,终得大功告成。
一大锅鹌鹑,五十斤左右,需要的糖油和香料不少。虽成本偏高,带来的利益却相当可观。
这也是江知味敢大胆用料的原因。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她想要快速积攒一波资本,就得逐渐往这些价钱稍贵的东西上转。毕竟口碑已经立下了,汴京又食客众多,来的那些老饕,都很乐意为她的吃食买单。
趁热打铁是最要紧的。
灶膛里的火舌不文不烈,日头升至头顶,园圃中韭菜和小葱的阴影渐渐只余下小小的一块。
容双闲来无事,在院子里给孩子缝红肚兜,用的正是先前江知味送她的布头。
当时那一跤摔的,起初还不觉得厉害,直到那尾巴骨过了七八日都还有些肿痛,她才后知后觉地心慌了起来。
尤其是在肚兜上穿丝引线的时候,她猛地意识到,就差一点儿,就见不到肚里的娃了,好在万幸。
灶房那头,有辣丝丝的鹌鹑香味飘出,夹杂着淡淡的牛乳香,似盛夏热烈的风中带着春雨润物无声的清爽。
之后那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物,都被江知味摆在小桌上。另端上来两大海碗的金沙炒饭,米饭上裹满了金灿灿的咸蛋黄,是他们今日的午食。
孩子们嗡地拥上来。
“哇,这就是牛乳甜点吗,真好看。”江暖歪了下头,“咦,怎么还不一样。”
指指这个:“二姐姐,这有褶子。”又指那个:“这个没有,还有那个,那个没褶子的还黄一些。”
“不仅长得不一样,味道也不同呢。”江知味把两小只抱到凳子上跪好,“都尝尝。”
勺子探到碗中。江暖小心翼翼地护着挖起的颤巍巍的乳白。她先吃了没褶子但略略发黄的姜撞奶,被牛乳中突然闯出的辛辣吓得皱了下眉头。
但很快适应下来,只觉得嘴里那东西冰凉又滑溜,明明进嘴的时候还有着颤动的外形,一和舌头相触,就水似的化掉,只余下牛乳淡淡的回甘。
“二姐姐,是姜啊。”
“好吃吗?”江知味眯眼微笑。
小鸡啄米似的脑袋点了又点:“好吃,吃了肚子里热乎乎的。”
她吃过后,一直在观望的凌花也大口下嘴,同样被牛乳里的姜味惊得呆怔住。初尝觉得好奇怪,怎么还能往牛乳里放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