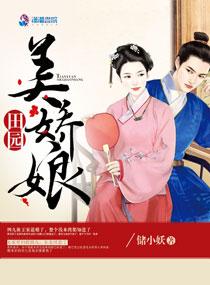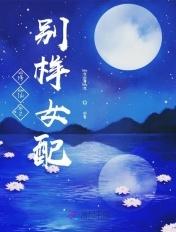我的书库>状元郎 > 第二百七十三章 不一样的入场(第1页)
第二百七十三章 不一样的入场(第1页)
贾知州不光提醒苏录,也命人提醒所有应试的童生,本次院试将空前严格,一定要遵守考纪,严肃作答,万不可心怀侥幸……
考生们大部分能听进去,但总有冥顽不灵者,只能说‘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了。
接下。。。
苏录立于金銮殿前,紫袍玉带,簪花披红,耳畔鼓乐喧天,眼前百官俯首。他望着那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心中却无半分得意之念。状元及第,万人称颂,可他知道,这不过是一场真正较量的开端。
礼毕退朝,新科进士列队入午门谢恩。沿途百姓夹道围观,争相一睹状元风采。有老儒拄杖而拜,口中喃喃:“斯文不坠,幸赖此人。”也有孩童被父母高举肩头,指着苏录喊道:“看!那就是咱们的状元郎!”苏录微微颔首,目光温和,却不曾停留。他的心早已飞向那尚未开启的仕途迷局。
回府途中,轿帘微掀,他望见街角一处茶肆,几个书生围坐议论,声音清朗可闻:“你说这苏录真敢在殿试上提‘清丈田亩’?那可是动天下豪族的根基啊!”另一人冷笑:“所以他才叫‘状元郎’,不是‘太平官’。可我倒要看看,他能在朝中活几日。”
苏录放下帘子,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他知道,自己已站在风口浪尖。那些藏在暗处的眼睛,早已将他视为异类??一个不懂规矩、不知收敛的寒门书生,竟敢以一纸策论撼动百年积弊。他们不会容他久居高位。
当夜,内阁大学士杨守礼遣人送来密信:“殿下虽重君才,然权柄仍在赵?之手。近日巡抚都御史已调兵布防江南诸府,名为缉盗,实为控势。君宜慎言谨行,待机而动。”
苏录读罢,默然良久。烛火跳动,映出他眉宇间的凝重。他取出随身携带的青布封套,轻轻展开那篇《君子务本》,指尖缓缓划过“舍仁义而专技艺者,譬如无舵之舟”一句,仿佛又听见父亲在田垄上的低语,听见陈?临终前那一声长笑。
“老师,学生来了。”他低声说道,像是对亡者承诺。
翌日清晨,吏部传旨:新科状元苏录授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三日后入阁侍读。此职看似清贵,实则远离实权中枢,历来为储相之选,亦是监视之所。苏录接旨叩谢,神色如常,心中却明了??这是皇帝的试探,也是赵?的安排。
果然,未及三日,风波骤起。
礼部侍郎周崇礼联名十三名御史,上疏弹劾苏录“妄议国政,淆乱纲纪”,指其会试文章中有“继富周富”之语,“影射朝廷偏袒权贵”,又言其与“逆党李景和交厚”,曾私传禁书《均田议》残卷,“心怀叵测,不宜近君侧”。
奏章递入宫中,朝野哗然。有人暗中冷笑,以为苏录必遭贬斥;也有人悄然叹息,知此乃清洗异己之始。
然而第三日早朝,皇帝却召集群臣,亲宣苏录对策全文,并问群臣:“如此赤诚之言,何罪之有?尔等攻讦新科状元,意欲何为?”
满殿寂然。赵?低头不语,周崇礼面如土色,只得伏地请罪。皇帝仅斥其“轻率妄奏”,罚俸三月,未予深究。而苏录,则被特许提前入阁侍读,参与编修《皇明政典》。
众人皆惊。谁也没想到,皇帝竟如此护短。
唯有苏录明白,这一场风波背后,另有玄机。那晚张福悄然来访,只说了一句话:“娘娘说了,好人该有个好前程。”他便已了然??宫闱之中,那一句轻描淡写的“好人”,胜过千军万马。
自此,苏录开始出入禁中,每日辰时入宫,申时方归。他讲《大学》,解《孟子》,言语平实,不尚虚华,却每每引古讽今,暗寓时弊。皇帝听得频频点头,有时竟命内侍记下其语,转交六部参酌。
赵?愈发忌惮。他原以为苏录不过一介书生,纵有才名,也不过是案头文章之徒,岂料此人竟能步步深入天听。更令他不安的是,苏录从不结党,亦不攀附权贵,连杨守礼几次邀其登门,他也婉言推辞。这般清绝姿态,反倒令人难寻把柄。
于是,赵?改换策略,不再明攻,转为暗制。
他授意户部尚书压下苏录所呈《江南赋役实录》,称“数据未经核实,不可轻动”;又命地方官府封锁民间田册,严禁私查田亩;更有甚者,派心腹伪装成江湖术士,在南京散布谣言,说“苏状元乃文昌星下凡,注定三载内横死,不得善终”。
一时间,流言四起。书院学子惶恐,亲友劝其低调。连远在山东的李景和也托人捎信:“子明兄,锋芒太露,恐招不测。暂避一时,或可保全。”
苏录读信良久,提笔回复八字:“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他没有退缩。反而在一次经筵讲学中,当着皇帝与诸阁老之面,直言:“三代以下,治乱兴衰,皆系于田制。井田虽难复,然均田限田,实为救时第一要务。若因惧豪强而不言,畏权势而缄口,则读书何用?为官何益?”
此语一出,满座动容。连一向沉默的兵部尚书都忍不住击节赞叹:“真丈夫也!”
皇帝沉吟片刻,忽问道:“依卿之见,若欲清查隐田,当从何处入手?”
苏录躬身答曰:“先试点一州,取信于民,再推及全省。臣愿亲往江南,督理此事。”
殿上一片哗然。赵?脸色铁青,正欲开口阻拦,皇帝却已点头:“准奏。着苏录以钦差身份,巡按南直隶常州府,专理田亩清查,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
圣旨一下,举朝震动。
赵?连夜召集亲信密议。有人主张立即刺杀苏录,以免后患;有人建议煽动地方豪绅群起抗命,使其寸步难行。最终,赵?冷笑一声:“不必动手。让他去查,查得越深,死得越快。”
他深知,江南之地,豪门盘根错节,一族之富,堪比国库。苏录孤身前往,既无兵权,又无地方根基,一旦触动利益,必将激起滔天巨浪。到那时,哪怕皇帝想保他,也无力回天。
苏录接到任命当日,闭门焚香,祭拜父母灵位。他取出父亲留下的《耕读图》,轻轻抚摸画中老农扶犁的身影,低声说道:“儿今日所行之路,正是您当年所望之世。纵九死其犹未悔。”
次日启程,百官送至城外。杨守礼握其手叹曰:“君此去,如孤舟入险滩,务必慎之。”苏录微笑:“学生记得‘君子务本’四字,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