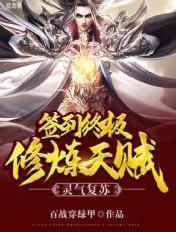我的书库>我为大明在续国运三百年 > 第133章 革新深水暗流潜涌(第2页)
第133章 革新深水暗流潜涌(第2页)
北海渔场,边军新业
北疆,黑龙江入海口及库页岛周边,昔日荒凉的海岸线,如今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岳武穆推行的“军转民,战转耕(商)”策略,在这里结出了硕果。随着边患缓解,大量熟悉水性、吃苦耐劳的前边防士兵,在朝廷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转向了海洋,开发被誉为“北海渔场”的丰富渔业资源。
朝廷通过新成立的“北疆商贸公司”下属的“渔盐司”,向退伍士兵和边民提供低息贷款,用于建造一种特制的、适应高寒海域风浪的拖网渔船。这种船比传统的近海渔船更大、更坚固,配备了改良的绞盘和更加耐磨的渔网。渔盐司还组织经验丰富的老渔民编写了《北海渔汛指南》,详细记载了不同季节鱼群的洄游路线、主要渔获种类(如营养丰富的鳕鱼、味道鲜美的鲑鱼、以及各种海蟹)和捕捞技巧,分发给各渔业合作社。
一个个由formersoldiers(前士兵们)自发组织或由官府引导成立的渔业合作社,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合作社的成员,往往是过去在一个卫所或烽燧并肩作战的袍泽,彼此信任,纪律性强。他们驾着新船,迎着凛冽的海风,驶向未知的深海。起初,难免遇到困难——恶劣天气的侵袭、渔场位置的判断失误、渔获保鲜技术的不足。但在官府的持续支持和自身摸索下,他们很快掌握了北海捕捞的规律。
码头上,建立了简易的加工厂。渔获上岸后,一部分新鲜的优先供应北疆驻军和新兴的城镇;大部分则按照传统工艺,进行腌制、晒干或熏制,制成易于储存和运输的咸鱼、鱼干。这些海产品不仅解决了北疆自身的食物供应,更通过“北疆商贸公司”的贸易网络,装上海船,南运至山东、首隶等人口稠密地区,甚至远销南洋。北海的鳕鱼干,因其价格实惠、耐储存,尤其受到欢迎。
昔日在马背上冲锋陷阵、在冰雪中戍守边关的悍卒,如今成了搏击风浪的渔场好手和精打细算的合作社成员。他们的收入显著增加,生活安定下来,许多人将家眷接来,在海边建起了新房。北疆的社会结构悄然改变,从纯粹的军事要塞,向军民融合、农商并重的繁荣边疆转变。地方财政也因此受益,渔税和贸易关税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真正开始实现“以边养边”的战略目标。
看到北海渔业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以及其在巩固北疆、开发东北、保障北太平洋航路安全方面的战略意义,卢象升正式上奏,建议在库页岛或黑龙江口择地设立“北海都护府”,超越单纯的军事管辖,统筹管理渔业生产、海上贸易、航道维护、移民实边以及对周边部落的抚慰事宜。朱由检览奏后,深以为然,立即批准。北海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大明对东北边疆及北太平洋沿岸的经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积极和系统的阶段。
间谍的价码,技术的壁垒
当大明在科技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欧洲各国宫廷和秘密机构里,则弥漫着一种混合了焦虑、羡慕和贪婪的复杂情绪。电报、蒸汽机、乃至传闻中那神奇的“电灯”,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在正面科研追赶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获取大明核心技术的渴望,使得技术间谍活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里斯本、阿姆斯特丹、伦敦的黑市和秘密沙龙里,关于大明技术的只言片语都被标以骇人听闻的高价。一份据称是“千里传信机”(电报)原理的潦草图解,几经转手,可能被炒到相当于一个中型庄园的价值;一块偷偷从报废明轮船上拆下的、带有铭文的“神龙西型”蒸汽机气缸铸件,更是被视为无价之宝,被各国间谍机构争抢。英国军情局甚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普罗米修斯之火”的绝密计划,目标是绑架一两位格物院的关键工匠,特别是参与过蒸汽机或电学研究的大匠,试图从其口中撬出秘密。
然而,大明对此早有防备。格物院及其下属的关键工坊,安保级别极高,由皇帝亲军和经过严格审查的侍卫层层把守,外人难以接近。所有参与核心项目的工匠和学者,都需有可靠的保人,并签署了严厉的保密协议。更重要的是,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网络无孔不入,不仅在国内严密监控可疑人员,其触角甚至延伸到了海外商站和航运线,使得欧洲间谍的行动举步维艰。偶尔有几起成功的渗透或收买案例,往往也很快被侦破,人赃并获,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即便有零星的技术细节或实物样本侥幸流出,欧洲人也沮丧地发现,他们缺乏复制这些技术的基础。制造一台高效稳定的蒸汽机,需要高精度的机床来加工气缸和活塞,需要特殊的冶炼技术来生产耐高压的锅炉钢板,需要系统的热力学知识来优化设计——这些,都是当时的欧洲工业基础难以支撑的。同样,没有对电磁学的深刻理解,没有成熟的玻璃密封和真空技术,即使拿到了电灯的外观图,也无法造出实用的产品。技术的代差,并非单纯靠逆向工程或间谍活动就能轻易弥补,它是一座需要整个工业体系和科学理论支撑才能攀登的高峰。
张骞从欧洲发回的情报,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困境:“……西夷诸国,于我方奇器,渴慕几近疯狂,间谍活动日炽,悬赏之巨,闻之咋舌。然观其内部,工坊技艺粗糙,理论探讨多停留在玄想辩论,缺乏系统实证。虽有零星仿制之举,然形似而神非,效率低下,故障频仍。故臣判断,西夷虽焦躁仿效,然其工基薄弱,理论混沌,短期内绝难成气候。然其执着之心、不择手段之志,亦不可不防,宜持续加强戒备,延揽其技工学者为我所用,反制其谋。”
星图微澜,前行不辍
静室之中,朱由检独自凝望着那幅关乎国运的星图。
代表电灯研究的那一点光芒,依旧在格物院的方向顽强地闪烁着,亮度增长缓慢,时明时暗,显然仍未突破那关键的材料瓶颈,未能形成稳定、扩张的光源。这预示着技术攻坚的道路依然漫长。
帝国内部,因科举改革而引发的思想动荡,在星图上清晰可见。原本稳定而浑厚的文教光域,此刻泛起了阵阵涟漪,光芒略显紊乱,显示出新旧观念碰撞带来的社会张力。一些代表传统士林力量的光点,甚至流露出些许晦暗和抵触的情绪。
然而,令他欣慰的是,北疆的光域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随着“北海渔场”的开发、屯垦的成功和边境贸易的繁荣,那片广袤土地的光芒更加凝实、明亮,边缘清晰稳定,甚至开始向周边的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辐射出温暖的光晕,显示出边疆地区正在从帝国的负担转变为坚实的支柱。帝国的整体光芒,虽然因内部的思潮波动而略有微澜,但根基深厚,主体光域炽盛强健,铁路和电报网络构成的光脉奔腾不息,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朱由检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都必然伴随着阵痛与阻力。技术的突破需要无数次的试错和长期的积累,无法急于求成;制度的革新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而最难的,莫过于思想的转变,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耐心以及成功实践的示范效应。
“不因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他轻声吟诵着,心中一片澄澈。他走到御案前,案上摆放着卢象升请求扩大“北海渔场”规模、增建港口的奏章,以及格物院例行呈报的、记录着最新一次灯丝实验失败细节的文书。
他提起朱笔,首先在卢象升的奏章上批了一个苍劲有力的“可”字,并批示:“北海兴利,实边富民,此乃长久之策。着北疆都护府会同户部、工部,详加规划,务求实效。所需款项,优先保障。”
然后,他展开格物院的文书,并未因那熟悉的失败记录而流露出丝毫失望。他在空白处,用朱笔写下了八字勉励之语:“但求精进,不问朝夕。”
这八个字,既是对格物院全体人员的殷切期望,也是他本人面对复杂局面的心境的真实写照。帝国的航船,在驶向未知深蓝的壮阔征程中,早己习惯了应对各种风浪与暗流。而这位坚定的舵手深知,唯有保持战略定力,不被一时困难所阻,不被眼前纷扰所惑,持续前行,不断积累,方能最终抵达那光明而遥远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