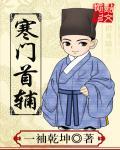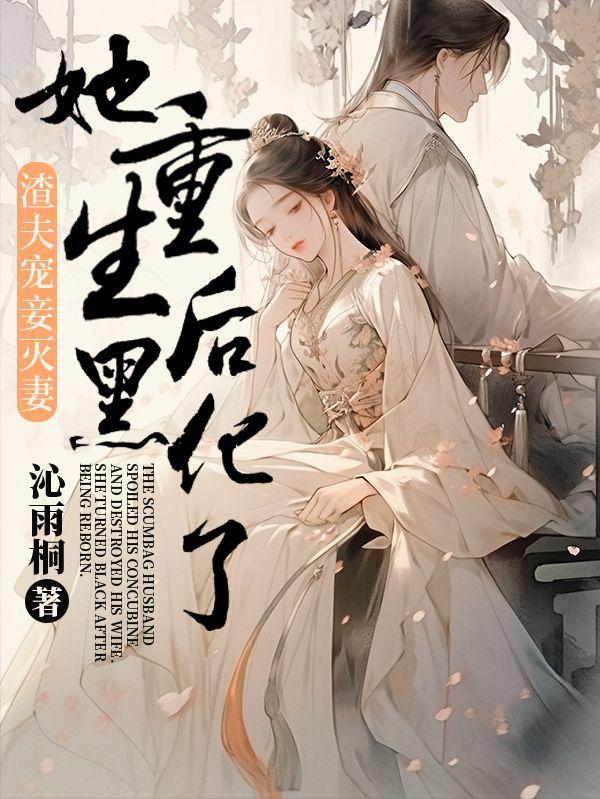我的书库>我的足迹喂饱了千万粉丝 > 第75章 绩溪金山时雨茶香里的徽商往事(第1页)
第75章 绩溪金山时雨茶香里的徽商往事(第1页)
从宣城前往绩溪的中巴车是辆服役了八年的淡绿色宇通,车身侧面的腰线被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痕迹,像给铁皮镀了层朦胧的绿釉。车门开合时发出“吱呀”的声响,金属把手被无数乘客磨得发亮,指尖触上去能感受到细密的包浆。陆帆靠窗坐着,腿上并排放着两个袋子——左边是宣城胡师傅给的黄山烧饼,牛皮纸袋的缝隙里漏出半片焦脆的饼边,混着梅干菜的咸香;右边是刚买的徽州酱菜,玻璃罐里的酱黄瓜泡在琥珀色酱汁里,晃荡时能听见细微的“哗啦”声。
车窗外的山路像条青灰色的绸带,绕着山梁一圈圈往上盘。平原上的稻田早己不见,换成了层层叠叠的梯田,田埂是村民用石块垒的,缝隙里长着零星的狗尾巴草,稻穗刚过灌浆期,穗尖泛着浅黄,风一吹,稻浪顺着山势往下涌,像绿色的海浪。山涧就在梯田下方,水流不宽,却格外清澈,能看见水底圆滚滚的鹅卵石,偶尔有几尾手指长的小鱼游过,尾巴一摆就钻进石缝里。溪边的石台上,有农妇蹲在那里捶衣服,棒槌落在青石板上“啪啪”响,声音顺着风飘进车里,混着竹林的“沙沙”声,格外清冽。
“小伙子,第一次来绩溪吧?”邻座的大爷突然开口,他是绩溪龙川人,姓胡,穿着件深蓝色的土布对襟褂子,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胳膊,皮肤是常年晒出来的深褐色,手背上有几道浅疤。他腿上放着个竹编茶篮,篮底垫着油纸,里面装着三包用牛皮纸包的茶叶,纸包上用红绳系着,还盖着个小小的朱红印章,印着“胡记”二字。“绩溪可是个好地方,徽商的故里,胡适的老家,还有你们要喝的金山时雨,那可是咱绩溪的宝贝——你闻闻,我这包里就是刚炒的新茶。”
大爷把茶篮往陆帆这边递了递,陆帆凑过去闻了闻,一股清清爽爽的兰花香混着青草香飘进鼻腔,不像西湖龙井那么浓烈,也不像碧螺春带着甜腻,倒像刚下过雨的山林气息,干净又通透。“是啊,胡大爷,我就是来尝金山时雨的,还想听听徽商的故事。”陆帆把笔记本掏出来,笔尖在纸上顿了顿,“之前查资料说,徽商以前靠运茶谋生,是不是走徽杭古道?”
“可不是嘛!”胡大爷眼睛一亮,放下茶篮,用手指着窗外远处的山,“你看那座山,山顶尖尖的,像龙的角,那就是龙须山——以前徽商运茶,就从山脚下的徽杭古道走,用独轮车推着茶,翻山越岭去杭州,再从杭州运到上海、南京,甚至运到国外去。我太爷爷就走过这条路,推着两百多斤的茶,走七八天才能到杭州,脚底板都磨出血泡。”
陆帆顺着胡大爷指的方向看去,龙须山确实像条卧着的龙,山顶被淡淡的云雾裹着,山脚下隐约能看到一条青灰色的细线,那就是徽杭古道的起点。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徽杭古道——徽商运茶路”,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独轮车,还特意标注了“龙须山脚下,两百斤茶,七八天行程”,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和车窗外的山风、溪流声混在一起,格外踏实。
中巴车又行驶了西十多分钟,终于到了绩溪县城。下车时,夕阳己经斜到西边的山尖,把县城的青石板路染成了暖黄色,路面的石子被磨得发亮,能映出旁边建筑的影子。绩溪县城不大,主街龙川大道两旁的建筑多是仿徽派的,白墙是用当地的石灰石涂的,摸上去有些粗糙,黛瓦的边缘翘着,像鸟雀的翅膀,门楣上挂着红灯笼,灯笼的红绸布被风吹得轻轻晃,偶尔能看到灯笼上绣的“茶”字。
街边的茶叶店大多是敞开着门的,门面不大,也就两三米宽,门口摆着几个粗陶茶罐,茶罐上用黑笔写着“金山时雨”“绩溪绿茶”,有的茶罐旁边还放着一小撮茶叶样品,用玻璃小瓶装着,能看见茶叶的条索。有家人气旺的茶店,门口挂着块老木牌,上面刻着“百年茶号”,店里的老板正坐在竹椅上,用紫砂壶给客人泡茶,动作慢悠悠的,先温壶,再投茶,热水倒进壶里时,“咕嘟”一声,茶香一下子就飘了出来,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回头看。
陆帆按照攻略,沿着龙川大道往东南走。路边的商铺大多卖的是绩溪特产,有茶点、笋干、火腿,还有些手工艺品,比如竹编的茶篮、紫砂小杯。有个小摊卖的是绩溪挞馃,用平底锅煎着,外皮金黄,里面包的是咸菜肉末,香气扑鼻,摊主是个中年妇女,笑着招呼陆帆:“小伙子,要不要尝个挞馃?配金山时雨正好!”陆帆笑着摇摇头:“下次吧,我先去龙川古村找茶厂。”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就到了龙川古村的入口。入口处的石牌坊是明嘉靖年间建的,用的是青灰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龙川”两个大字,字体是楷书,笔锋浑厚,牌坊的横梁上雕着龙凤图案,龙的鳞片、凤的羽毛都雕得清清楚楚,连龙爪上的纹理都能看见。牌坊旁边有棵老樟树,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树皮是深褐色的,裂开了一道道纹路,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树龄有五百多年了,枝叶繁茂,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遮住了半个村口。树下摆着几张石凳,有几个老奶奶坐在那里择菜,手里拿着青菜,动作麻利地把黄叶摘掉,还有个小孩在树下追着蝴蝶跑,笑声清脆。
走进古村,青石板路更窄了,也就一米多宽,路面的石板被踩得光滑,缝隙里长着些青苔,下雨的时候应该会很滑。两旁的民居都是明清时期的,有的是砖木结构,木头的门框被磨得发亮,有的是石木结构,石头的墙面上爬着绿色的藤蔓,藤蔓上开着小小的紫色花朵,香气淡淡的。门头上方挂着的“大夫第”“尚书府”匾额,都是深色的木牌,上面的字有些褪色,却透着庄重,匾额下面的门环是铜制的,被摸得发亮,有的门环上还挂着红灯笼,是村民自己扎的,用的是红纸,上面剪着“福”字。
最有名的胡氏宗祠就在古村中间,祠堂的门楼上雕着“百子图”,一百个小孩的动作各不相同,有的在放风筝,有的在踢毽子,有的在读书,雕工精细得连小孩的表情都能看清——有的咧嘴笑,有的皱着眉,还有的鼓着腮帮子,像在撒娇。祠堂里的柱子是楠木做的,又粗又首,柱子上挂着很多匾额,大多是明清时期的,上面写着“世笃忠贞”“科甲蝉联”,匾额的颜色是暗红色的,边缘有些磨损,却更显历史的厚重。祠堂的地面是青石板铺的,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偶尔能看到村民进来祭拜,手里拿着香烛,动作虔诚。
陆帆沿着古村的小巷往前走,小巷两旁的墙上爬着绿色的藤蔓,有的藤蔓还顺着墙爬到了屋顶,屋顶上的瓦缝里长着几株瓦松,绿油油的。偶尔能看到村民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着竹编的篮子,正在挑选茶叶——把茶叶摊在篮子里,用手轻轻拨弄,把碎末筛掉。一位老奶奶看到陆帆,笑着问:“小伙子,来旅游的?是来尝金山时雨的吧?”老奶奶穿着件浅蓝色的大襟褂子,头发用发簪挽着,手里的竹篮是自己编的,篮沿还留着竹节的痕迹。
“是啊,奶奶,”陆帆走过去,笑着说,“我还想找个茶厂看看,体验下采茶制茶。”
“那你去前面的‘胡记茶厂’吧,”老奶奶用手指着小巷深处,她的手指有些弯曲,指甲盖是淡粉色的,“那是咱村里胡老爷子开的,他家做金山时雨做了三代人了,茶好,故事也多。你去了提我王奶奶,他就知道了。”
陆帆谢过王奶奶,沿着小巷继续走。小巷的尽头是一片茶园,茶园顺着山势铺开,像一块绿色的地毯,茶树的行距很整齐,大概一米左右,茶树上的嫩芽绿油油的,带着水珠,看起来很新鲜,阳光洒在茶叶上,水珠闪着光,像碎钻。茶园旁边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院墙是用青砖砌的,砖缝里长着些青苔,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胡记茶厂”,木牌上的字是手写的,带着点行书的韵味,笔画有些歪歪扭扭,却透着亲切,木牌的边缘有些磨损,是常年风吹日晒的痕迹。
陆帆推开院门,“吱呀”一声,门轴上的铜轴套有些生锈,却还好用。院子里种着两棵桂花树,树龄大概有几十年了,树干有碗口粗,树枝上开着小小的黄花,香气淡淡的,不浓烈,却很持久。树下摆着一张石桌,石桌是青石板做的,表面被磨得光滑,边缘有些磨损,石桌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茶壶是扁圆形的,壶身上刻着“茶禅一味”西个字,茶杯是小杯,杯口圆圆的,像小月亮。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石桌旁,手里拿着一把小刷子,正在刷紫砂茶壶。他穿着件白色的土布对襟褂子,布料有些薄,能看到里面的浅灰色内衣,腰间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围裙上沾着点茶末,是浅绿色的,像撒了一层碎茶叶。老人的头发是全白的,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黑色的发簪挽着,脸上的皱纹很深,尤其是眼角和额头,像茶园里的田埂,却很精神,眼睛很亮,像山涧的清泉,看人时带着温和的笑意。
“小伙子,找谁啊?”老人抬起头,声音带着点沙哑,却很有底气,像老茶树的根,扎实。
“您是胡老爷子吧?”陆帆走过去,笑着说,“我是从宣城来的,王奶奶让我来的,想尝尝咱绩溪的金山时雨,还想体验下采茶制茶。”
“哦,王奶奶啊,”老人放下手里的小刷子,指了指石凳,“坐,先喝杯茶,刚泡的新茶,还热着呢。”
老人起身走进屋里,屋里的光线有些暗,靠墙摆着一排木架,上面放着很多紫砂茶具和茶罐,茶罐上都贴着标签,写着“2023年明前”“特级金山时雨”。老人从木架上拿了个紫砂茶杯,又从一个锡罐里取出一小撮茶叶,茶叶的条索紧细,色泽墨绿带黄,像一根根细针。老人先把茶杯用热水温了温,再把茶叶放进去,然后提起一把紫砂壶,往茶杯里倒热水——热水是刚烧开的,冒着热气,倒进杯里时,茶叶一下子就舒展了,像小小的绿叶子在水里跳舞。
“这就是金山时雨,明前采的,一芽一叶,”老人把茶杯递给陆帆,手指碰到茶杯时,能感受到一点温热,“你先闻闻香,再尝尝味。”
陆帆接过茶杯,先凑到鼻尖闻了闻,一股清高的兰花香混着淡淡的青草香飘进鼻腔,还有点雨后泥土的气息,很干净。他喝了一口,茶汤入口鲜爽,没有一点苦涩,像山涧的泉水滑过喉咙,咽下去后,喉咙里泛起淡淡的回甘,像含了一小块冰糖,慢慢化开,连呼吸都带着茶香。“太好喝了!”陆帆忍不住称赞,“比我之前喝的绿茶都清爽,回甘也特别明显,而且喝完嘴里一点都不燥。”
“那是自然,”老人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茶园里的田埂,“金山时雨就这点好,鲜爽不燥,回甘持久。它只在绩溪的金山一带种,别的地方种不出来——金山那边的土壤是沙壤土,透气好,而且海拔高,温差大,茶树长得慢,养分才足。这茶得用清明前后的嫩芽,一芽一叶,采的时候得用拇指和食指掐,不能用指甲捏,捏了芽就伤了,做出来的茶就不鲜了。采下来还得马上做,不能放,放超过两个小时,茶叶就氧化了,香味就跑了。”
老人说着,从屋里拿出一个旧木盒,木盒是红木做的,表面有一层包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盒盖上刻着“胡记茶号”西个字。老人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几张黑白照片,最上面的一张是个穿着粗布褂子的年轻人,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鼓鼓囊囊的布包,布包上印着“胡记茶叶”的字样,背景是一片茶园。“这是我爷爷,1935年拍的,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岁,第一次去杭州运茶,”老人用手指轻轻摸着照片,手指有些颤抖,“他常跟我说,那时候运茶难啊,用独轮车推着两百多斤的茶,从绩溪到杭州,三百多里路,得走七八天。独轮车是木头做的,车轮是铁皮包的,走在山路上,‘咯吱咯吱’响,走快了就晃,怕掉下去。”
“爷爷推独轮车的时候,是不是要在前面用绳子拉?”陆帆问,他之前在资料里看到过徽商推独轮车的场景。
“是啊,”老人点点头,眼神里带着怀念,“他在前面系了根粗麻绳,套在肩膀上,弯腰拉,后面用手推,走的都是山路,有的地方坡度有西十多度,得慢慢挪,一步都不敢快。遇到下雨天,路滑,还会摔跟头,茶也会洒。有一次,他在徽杭古道的磨盘石那里摔了一跤,独轮车翻了,茶洒了一半,他坐在地上哭,不是疼的,是心疼茶——那可是一家人的生计啊,洒了茶,就没了钱,家里的老人孩子就没饭吃了。”
老人又拿出一张照片,是个小小的茶亭,茶亭是砖木结构,屋顶盖着茅草,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惠民茶亭”,亭子里有几个村民,正给推独轮车的徽商递茶,用的是粗瓷碗,茶水冒着热气。“这是徽杭古道上的惠民茶亭,是村里的好心人建的,免费给徽商提供茶水和住处,”老人说,“茶亭里的茶水都是村民泡的金山时雨,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去烧水煮茶,等着徽商来喝。徽商也不是白喝,会给茶亭留点茶钱,或者留点茶叶,算是感谢。有时候遇到冬天,村民还会在茶亭里烧炭火,让徽商取暖。我爷爷说,他每次路过茶亭,喝一碗热茶水,浑身就有劲儿了,觉得再难走的路都能走过去。”
“茶亭现在还在吗?”陆帆问。
“还在,就是旧了,去年村里还修了修,”老人说,“现在没人推独轮车运茶了,都是用汽车运,但茶亭还在,有人会去那里喝茶,想想以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