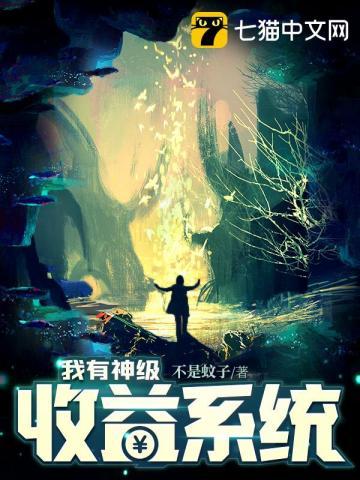我的书库>盐祸猪六戒 > 1020(第26页)
1020(第26页)
一把大锁将李执事的家锁得死死,好在沈亭山还有溜门撬锁的本领。
陈脊称叹道:“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
沈亭山摸了摸鼻子,作沉思状,随后一本正经说道:“好像没有,我是无所不能的。”
陈脊啐道:“给你三分颜色你倒真开起染坊来了。”
沈亭山将门推开,大摇大摆走在前头,朗声道:“你这人有趣。不承认我无所不能,又非要称赞我有什么不会的。我告诉你,我就算是孙猴子也有那飞不出的五指山。”
陈脊笑着,无奈地摇摇头,跟着沈亭山进了屋。
李执事的家不大,但屋中的陈设可谓尽奢华之能事,房中挂有不少名家字画,几案上的花口瓶插着的并非鲜花,而是精美的金银编圈牡丹,柜上的杯盘壶盏也均是上品,与金凤楼的厢房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脊扫视了一圈,疑惑道:“我上次来这还不是这样的呀。”
沈亭山拿起一个缠枝纹青花瓷瓶,笑道:“这些东西成色尚新,看来他是最近刚发得大财。”
“你看,”陈脊从柜中搜出一份地契,“他几日前还购置了新的房产。”
“一个刚购置了房产的人……你想想,会是什么人?”
陈脊想了片刻,说道:“短期内不会远行,在本地能站稳脚跟。”
“等等!”沈亭山在柜中翻寻,又看到了一张卖房契,两张房契比较,竟是同一个地方。
“这李执事刚买的房子又卖了?而且,还是亏本出售。”陈脊看着沈亭山,眉头紧皱。
“再找找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随后,沈陈二人又陆续在房中找到了许多当票,根据这些当票所示,李执事几乎在短短的二天内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看来这屋里剩下的都是带不走的东西。”
“或者,是这些东西还不够值钱。”沈亭山挑挑眉,接着说道:“他一个小小的执事,纵使靠着盐荒发了大财,也不会富裕到这种地步。”
沈亭山说着,又从祭拜的香炉中捡到一角尚未完全燃尽的信纸。
沈亭山借着日光仔细端详,那信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可以辨认出是一个“杀”字,“也许,他是在这赚的钱。”
陈脊闻声凑过来看,这字迹让他觉得有些古怪,“这字迹……”
沈亭山顿了顿,说道:“这字迹有些眼熟,你想得起来吗?”
陈脊凝眉忖思了一会,无奈地摇摇头,“确实见过,可记不得是何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陆庠生的字,也不是崔娘的字。”
沈亭山笑道:“可以吖,你什么时候见过崔娘的字迹了?”
陈脊挠了挠头,憨笑道:“昨夜在金凤楼,我瞧见中央舞台后头挂着一幅蝶戏图,落款就是崔娘。”
陈脊说着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转身钻入卧房,在李执事的衣橱中一阵搜查。
“你看!”陈脊叫来沈亭山,“他贵重的衣服和丧行行服都留在这,倒是平日里我见他穿过的几件朴素的衣服不在。”
“你有什么猜想?”沈亭山鼓励陈脊大胆说出来。
陈脊咽了咽口水,满脸不自信的说道,“他应该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所以着急换了钱财。但路上又不想引人注目,所以只带了朴素的衣衫。我如今安然无恙,说明李执事并非从我这笔交易中获利。他能有这许多钱,想必就与那张纸条有关。”陈脊说着加重了语气,“另有人雇佣他杀害其他目标。不过,这个‘其他目标’是谁,是否与裴荻和皮三儿有所关联,尚且无法断言。”
沈亭山眼睛里闪烁着赞许,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先把这字拿着,”说着又将纸小心装入阴阳葫芦里,“一个‘杀’字,不管与这案子有没有关系,反正不是好事。”
陈脊没有立时接话,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沈亭山的葫芦,半晌,吞吞吐吐道:“我能喝你一口酒吗?”
沈亭山微怔了一下,笑道:“想喝你就直接拿去,莫说一口,便是与你痛饮十坛又如何?”
陈脊伸手接过沈亭山递来的葫芦,神色有些尴尬地呷了一口,“一口就够了,还要查案呢。”
沈亭山察觉出陈脊的异样,歪头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怎么了?”
陈脊低下头,心虚地眨了眨眼,慢吞吞道:“这案子真的能查出真相吗?”
沈亭山抿了抿嘴,直起身子,将陈脊拉到桌旁坐下,语气深沉地开口道:“我明白你的担忧。李执事这案本就难破,何况他还牵扯着裴荻案和皮三儿案。从盐商会到药行又到打行,从私盐贩子到官场贪腐,确实纷繁。”
“这幕后之人如果是是不能查的呢?”
沈亭山闻言,紧绷的脸忽然松了下来,笑道:“什么是能,什么是不能?”
陈脊顿了顿,这话让他忽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不能查的是什么?好像就算背后之人是陛下也没有什么不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