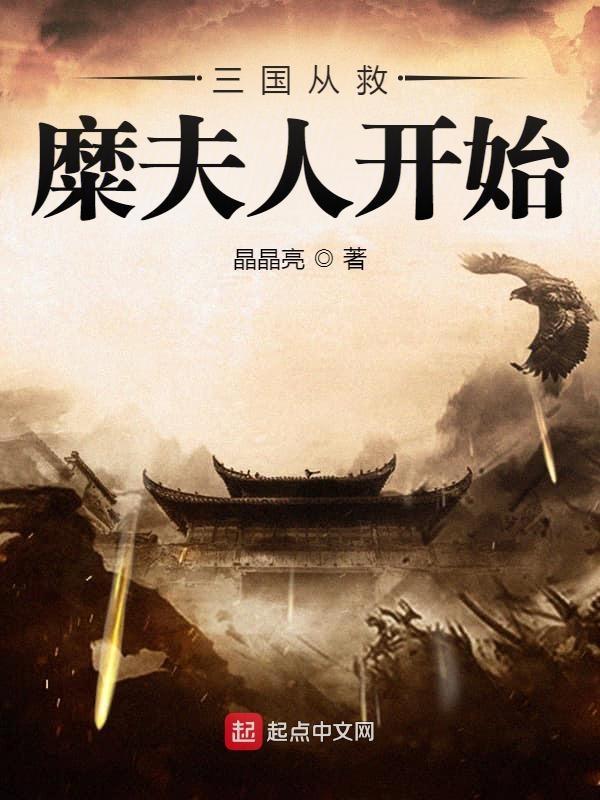我的书库>死对头穿成我的猫 > 1620(第28页)
1620(第28页)
他似乎不需要睡眠似的坐到半夜,直到谢松亭和两只猫完全睡熟,才去拿打开的快递。
盒子里放着一个平安符,底下垫着些拉菲草。
平安符平平无奇。
大红色,封口有金箔绣线。
席必思打开符包,拿出里面的东西,动作堪称小心翼翼。
是一根丝。
金色,半透明,有粗有细,不规则,不均匀,像天然的蚕吐出来的半成品蚕丝。
他手很稳,把它送到谢松亭唇边,轻微触碰。
甫一接触人,金丝宛如活物,摇头摆尾,化作金色的、发亮的雾,缓慢流入睡着的谢松亭口中。
直到漆黑的夜里再无一丝亮光,且谢松亭没有任何不适反应,席必思才松了口气。
他抹去额头热汗,矮下身,隔着被子把谢松亭抱紧。
之前几天,他做的最多的也就是抱他,从不逾矩,今天却一反常态,贴着谢松亭的额头,和他鼻尖相抵,释怀地吐了口气。
金丝就像一道界限,将他们之间隐形的屏障打破。
睡着的谢松亭本能地推他。
席必思不顾他的抗拒,将人抱得更紧,鼻尖一错,用舌润湿另一个人的唇瓣。
他着迷地轻轻一吻,很快脱离,起身去客厅,坐在沙发上吹冷风。
一对猫耳一会儿后飞,一会儿兴奋得一抖一抖。
是在高兴。
特别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