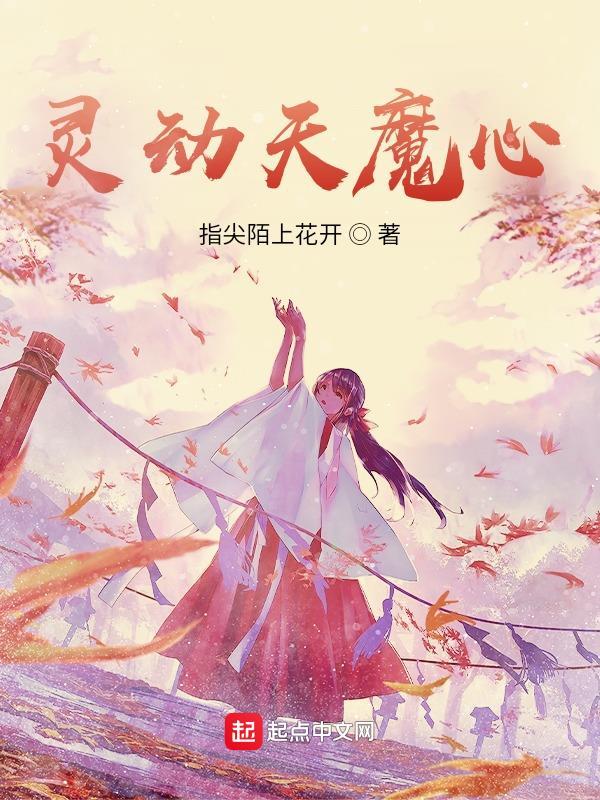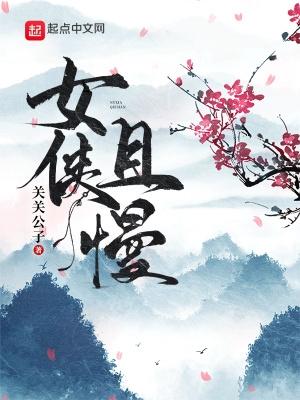我的书库>无敌从降妖除魔开始 > 第239章 祂在醒来(第1页)
第239章 祂在醒来(第1页)
有岩浆就在阿姐的旁边掀起,吓得她直接挂在了姜望的背上,而姜望与锋林书院首席掌谕也顺势掠起,躲闪着各地随时涌出的岩浆以及劈落的雷电。
而裴静石仍在原地没有动作。
天上有雷电劈落,无形的剑气直接将其消弭。
有岩浆涌来,也被剑气防住。
他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反应。
姜望瞥了他一眼,然后就看向仍在僵持的黄小巢与漠章,说道:“看来黄统领的实力还是差着裴剑圣许多。”
就算漠章没有被裴静石打成重伤,但也受伤了,状态是肯。。。。。。
海潮又一次漫上沙滩,又缓缓退去,如同时间本身在呼吸。那行机械巡吏留下的脚印早已被浪冲散,可新的足迹却不断出现??有赤足孩童的,有草鞋老农的,也有穿铁靴的密探。他们来此并非为了朝拜,也不是为求药问病,而是为了一个词:**听见**。
钟舍门前的小院不再冷清。每日清晨,总有人悄悄放下一只陶罐、一束干花、或是一张写满字的麻纸,然后悄然离去。有的是感谢信,说昨夜梦见母亲笑了;有的是控诉书,记录村中“理性督导员”强行带走疯癫诗人;还有的只是简单一句:“我开始怀疑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沈知晦将这些一一收下,不加评判,只命人誊抄副本,送入地下密室封存。
他依旧每日煮茶,坐在檐下看日出。白雪衣则常立于礁石之巅,手中断剑虽无锋刃,却能感应百里内灵波异动。她曾说:“如今最可怕的不是刀兵,是无声的驯化。”这话后来成了回声会成员口中的箴言。
这一日,天光微明,雾未散尽。一名少年自南而来,浑身泥泞,肩头渗血,怀里紧抱一卷竹简。他在门前跪了整整一夜,直到晨钟响起才被发现。
“我是岭南‘哑钟书院’的学生。”他声音嘶哑,“我们老师……昨夜被带走了。临走前,他让我把这东西送到您手上,说只有您懂它的意思。”
沈知晦接过竹简,轻轻展开。上面并无文字,只有一幅手绘图:一口倒悬之钟,钟口朝天,铃舌却指向大地,下方刻着一行小字??
>“当钟不再为人而鸣,便要为地而响。”
他闭目良久,指尖轻抚图纹,仿佛触摸到了那位素未谋面的书院主人的心跳。那是一种决绝的意志,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
“你们书院教什么?”他问。
少年低头:“我们教孩子读旧典,讲白砚秋如何以法抗神,讲青鸾为何宁死不愿签署‘和平契约’。我们也教他们辨识官府发布的‘标准情绪模板’,告诉他们:哭可以不是软弱,笑也不一定是快乐。”
沈知晦点头,转身取出一枚铜铃,交予少年:“回去吧。把这挂在书院最高处。若有一天,你们决定让钟落地,就敲它三声。”
少年含泪而去。
七日后,南方传来消息:哑钟书院遭突袭,十二名师生被捕,其余学生四散逃亡。但就在执法队砸毁最后一根梁柱时,那枚铜铃竟自行震颤,发出一声低沉长鸣。据附近村民描述,那一刻,方圆十里内的井水突然沸腾,鸟群齐飞,连聋哑多年的老人也捂住耳朵,喃喃道:“好响……真好响啊。”
更诡异的是,当晚全国三百余座废弃古钟同时共鸣,哪怕深埋土中、锈蚀断裂者亦未能幸免。秩序司紧急封锁数据,称系“地磁异常引发共振”,可民间已有传言四起:
>“钟醒了。”
>“它们记得。”
>“有人在替我们说话。”
沈知晦听闻此事,并未多言,只是命人取来七色丝线,亲手编织了一条护符,放入新制的小钟内部。他说:“从今往后,每一声钟响,都该承载一个人的真实。”
此时,回声会已发展至万余人,遍布十七州郡。他们不再只是被动记录,开始主动设问。一些教师在课堂上提问:“如果所有人都说黑是白,那你还坚持看见的是黑吗?”狱卒们则在交接班时低声传递囚犯遗言;渔夫们用暗语在捕鱼歌谣中嵌入被禁的历史片段;甚至有工匠在铸造铁锅时,悄悄刻下“不准自称正确”五字,待买家刮去锅底焦垢,方得见真言。
这一切如细流汇江,悄然冲击着“共识之灵”的统治根基。
然而,真正的裂痕出现在一年后的“清明公审”。
那是朝廷为震慑异端所设的一场公开审判,地点选在中原重镇洛京广场。被告是一名年仅十九岁的少女,罪名是“传播非理性信仰”,证据是她在街头向路人分发手抄版《钟舍问答录》。官方宣称,此案将全程直播,由AI系统“明镜判官”主持,确保绝对公正。
数千万人通过玉简接入观看。
庭审开始后,一切如常。AI以冰冷逻辑逐条驳斥少女言论,指出其主张缺乏实证支持,易引发群体焦虑。观众席上多数人神情漠然,仿佛只是观看一场例行程序。
直到少女开口陈述。
她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我想讲一个故事。关于我娘。她是个织女,每天要在机器旁站十个时辰。三年前,她开始做同一个梦:自己变成一只鸟,飞过雪山,落在一口铜钟上。每次醒来,她都会流泪。医生说她是‘情感溢出症’,开了药。吃药之后,她不再做梦,也不再哭了。但她看着我的眼神,像看着陌生人。去年冬天,她死了。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我没留住那个梦。’”
她顿了顿,抬头望向虚空中的镜头:
“我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但我知道,当一个人连悲伤都不能自由表达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正确,一定出了问题。”
全场寂静。
下一瞬,异变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