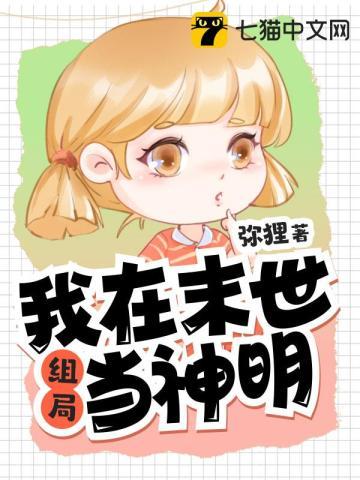我的书库>重生后,她成了权臣黑月光 > 第691章 前世的女儿(第2页)
第691章 前世的女儿(第2页)
宫门前,禁军列阵阻拦。领头将领认出她面容,犹豫片刻,终是放行。阮凝玉步行入殿,一路穿过重重宫门,两旁宦官宫女皆低头避视,似惧其目光灼人。
太极殿内,太后端坐高位,脸色苍白,显然病体未愈。阶下群臣肃立,裴仲衡虽已被革职,其党羽犹存,此刻个个面露讥讽。
“阮氏女子,擅闯宫禁,可知罪?”左相厉声喝问。
阮凝玉不跪,昂首道:“我非擅闯,而是奉召而来。太后曾问我想要什么,我说不要封赏,只要民声得通。今日我来,便是要问一句:您给的诏书,算不算数?”
满殿哗然。
太后闭目片刻,轻声道:“你说。”
“谢允尚书何在?”
“病重休养,不便见客。”
“那请容我告知诸位大人??”她转身面向群臣,声音陡然拔高,“就在昨夜,我以通灵之术窥见真相:谢允并未生病,而是被囚于地牢,遭受‘噬音刑’??每日以镇魂鼓轰击耳膜,直至彻底失聪,沦为废人!而幕后主使,正是你们之中那些口称礼法、实则惧怕民声的伪君子!”
“放肆!”右相怒拍桌案,“妖女妄言,蛊惑圣听,来人,拿下!”
禁军上前,却被太后抬手制止。
她睁开眼,目光如刃:“让她说完。”
阮凝玉从怀中取出一枚玉片,托举过顶:“此乃《天籁原典》残页,记录了一条被删改的古训:‘凡以声止声者,其心先聋;以权压音者,其国必亡。’今日我愿以此玉为证,请求开启‘鸣冤台’,举行‘对音大审’??让我与指控我的人,当庭以乐辩理,以音证心!若有半句虚言,甘受五雷轰顶!”
殿内寂静如死。
所谓“对音大审”,乃是上古典制,唯有涉及礼乐根本之争时方可启用。一旦开启,双方须各奏一曲,由太庙铜鼎鸣响为判:若鼎自鸣,则言真;若无声,则为妄。
这是赌命的较量。
良久,一名白发老臣走出队列,正是曾主持焚谱的礼部老尚书:“老臣附议。既然她敢提此议,便让她试试。若铜鼎不响,便是欺天,当场诛杀,永绝后患。”
“准。”太后缓缓点头,“三日后,鸣冤台开审。”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百姓争相涌向皇城广场,搭建临时看台。心音书院的学生们连夜赶制banners,上书“还我声音”“听心无罪”。而与此同时,各大酒楼茶馆流传起新的谣言:阮凝玉实为北狄细作,欲以音律操控人心,颠覆社稷。
第三日午时,鸣冤台升起于太庙之前。高台两侧设双琴,中央立一尊三丈高的青铜鼎,鼎腹刻有“听天下”三字。观者逾十万,连宫墙之上都站满了人。
阮凝玉一袭素衣登台,发间别一支银簪,乃是母亲遗物。对面,代表朝廷出战的是太傅门生、年仅十七岁的“神童乐师”沈清越。少年面容俊秀,指尖修长,据说能同时弹奏七弦而不乱分毫。
主审官宣读规则后,沈清越率先抚琴。他奏的是一曲《清平调》,旋律优美庄重,合乎礼法,听得众臣频频颔首。琴毕,铜鼎静默如初。
轮到阮凝玉。
她并未急着拨弦,而是缓缓摘下发簪,轻轻划破手指,将血滴于琴弦之上。刹那间,琴身微震,发出一声低吟,仿佛痛极而泣。
她闭目,开口唱起一首无人听过的歌:
>“娘走那天,河结了冰,
>我在岸边,喊不出声。
>她回头望我,眼里有星,
>可风太大,吹散了名……”
歌声朴素,近乎嘶哑,却带着一种撕裂灵魂的力量。台下有人开始抽泣,有老兵捂住耳朵颤抖,有妇人抱着孩子低声应和。
当唱至“她们烧了我的谱,却烧不断我的根”,她猛然拨动主弦??
“嗡??”
一声巨响,青铜鼎竟自行震颤,第一道音波扩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