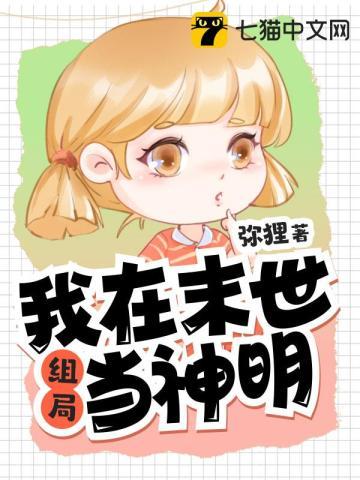我的书库>重生后,她成了权臣黑月光 > 第691章 前世的女儿(第1页)
第691章 前世的女儿(第1页)
眼见谢凌并没有计较慕容深给她通信的事。
烧毁了这封信,谢凌便回了居室,阮凝玉又端来了一碗药给他喝。
她端着药,将苦涩的药汁一点点喂进他的唇里,眼见他回来的这个过程里始终面色如常,她便觉得宽心许多。
阮凝玉面色缓和,谢凌比她大了多少岁,他定不会因为这点小情小爱生气的。
他适才因穿着中衣便出来,受了点冷风,此时许是因为急火攻心,喝完了药,坐在榻边,用手掩唇,竟咳出了一点血。
阮凝玉变了脸色。
“谢凌!”
她。。。。。。
冬雪未消,长安城外的官道上覆着一层薄霜,晨雾弥漫如纱。归晚楼前那株老梅已落尽残花,枝头却凝着几点晶莹??是冰,也是泪。自“万籁祭”之后,朝廷虽颁诏废除乐禁,然旧势盘根错节,暗流从未真正平息。民间欢腾之际,阮凝玉却知,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
她独坐琴室,指尖抚过新制的七弦琴。此琴以沉水香木为体,嵌九枚音骨,据说是上古乐人取战死者喉骨所炼,能引亡魂共鸣。阿弦曾劝她莫用此器:“太过阴厉,伤己亦伤人。”可她只淡淡一笑:“若世间清明,何须黑月光照?”
这几日,各地奏报陆续传回:心音书院在洛阳遭纵火,三名女学生葬身火海;江南巡抚以“防蛊惑民心”为由,拒发乐籍执照;更有御史弹劾太后“崇妖乱礼”,称《天籁原典》乃“邪术幻象”,应焚毁以正纲常。而最令她心惊的是,谢允接连三日未上朝,宫中传言他染疾卧床,实则连贴身小太监也无法近身。
“他在躲什么?”阮凝玉望着案上一封密信,字迹潦草,仅一句:“钟楼将哑,桥断于东。”
她立刻召来桃夭与阿弦。归晚楼地窖早已改建为“九音堂”,墙上挂满各地传来的民谣手抄本,地下埋设铜管,可听百里之外的风声水响。三人围坐于阵图中央,点燃一炉沉香,借烟形推演局势。
“钟楼将哑,是指皇权不再发声。”阿弦盲眼微颤,“桥断于东……东华门向来是权臣出入之所,莫非谢允已被囚?”
桃夭咬破指尖,在黄纸上画出一道血符:“我昨夜梦到母亲。她说‘金丝笼开,真凤不归’。这不像吉兆。”
阮凝玉沉默良久,忽问:“春桃呢?”
“她在城南教孤女们唱《朝阳歌》,说要让每个孩子都记得自己是谁的女儿。”
“去把她叫回来。”阮凝玉起身,走向密柜,“该用那东西了。”
柜中藏的是一具人皮面具??并非易容之术,而是用死去乐师的脸皮制成,相传佩戴者可听见逝者临终前所闻之声。这是焚音令时期,一位老乐工拼死留下的遗物,也是“九音使”最后的秘法之一。
“你要通灵?”阿弦震惊,“那会折寿!”
“我不怕折寿。”她将面具轻轻覆上面颊,瞬间,四周空气骤冷,烛火转青,“我只怕桥断了,再没人敢接下一程。”
子时,九音堂燃起九盏白烛,按北斗方位排列。阮凝玉盘膝而坐,手持断笛,吹奏《万象听心录》中最晦涩的一段??“唤魂调”。笛音低回,如泣如诉,穿透地底铜管,直抵京城每一处被遗忘的角落。
忽然,风起帘动,空中浮现出模糊影像:一座幽深地牢,铁链缠绕四壁,一名灰袍男子跪伏于地,背上烙着“逆音”二字。正是谢允!
他口中喃喃,似在背诵某段古老律文:“……音者,天地之心也。王者听之,则政清;庶民歌之,则怨散。禁声者,实禁心也……”
画面一转,出现一座隐秘殿堂,殿中供奉着一尊青铜巨鼓,鼓面绘有人脸,双眼空洞,嘴角下垂。数十名身穿黑袍的老者环绕而立,齐声吟唱某种反律咒语。鼓每响一声,便有一处心音书院的灯火熄灭。
“摄魂会……”阿弦牙齿打颤,“他们还没死绝。”
桃夭猛地站起:“那是裴仲衡背后真正的主子!那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权力,他们是恐惧??恐惧百姓有了声音,就不再需要他们来代言!”
阮凝玉强忍头痛,继续凝视幻象。只见谢允突然抬头,望向虚空,仿佛直视着她的眼睛:“凝玉,若你看见这一幕,请记住:钟楼不会自己发声,它需要一个愿意为之赴死的人去敲响。我不是被困,我是自愿入局。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逼他们现出真形。”
话音未落,画面崩裂,面具“啪”地碎成粉末,洒落一地。
阮凝玉呕出一口黑血,却被她迅速掩入口帕。“准备车马。”她擦去唇角血迹,“我要进宫。”
“你疯了!”桃夭拦住她,“你现在进去,就是送死!”
“正因为我知道是死局,才必须去。”她冷笑,“他们想让我逃,好坐实‘畏罪潜逃’的罪名。可我要光明正大地走进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告发,不怕审判,更不怕死亡。我们要的是真相当庭昭雪。”
次日清晨,一辆素辇缓缓驶向皇宫。车上无旗无号,唯有一面铜镜悬于车顶,映照朝阳。百姓见之,纷纷跪地叩首??那是“心音为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