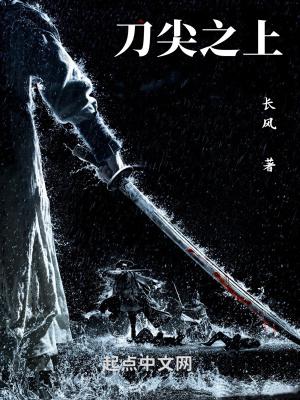我的书库>咸鱼她字字珠玑 > 第185章(第1页)
第185章(第1页)
但贾逊却没答应。一来,他知晓这承平道是叶氏手里的人,眼下时局未清,他不好贸然动手。二来,承平道虽在溟西散布传言,但归根结底是在促进溟西同南沙的生意,与其在意这些不痛不痒的名声,还是银子流进兜里最为实在。至于这第三嘛……
贾逊提着华袍,跟着观里接应的侍从拐至偏堂。
至于这第三,那就是贾逊看上了承平道的信众。在溟西,贾氏尚可一手遮天,但放眼整个大周,除了枭雄叶氏,如今最为惹眼的便是承平道这位行踪不定的清也先生了。
要是能同他将关系做好,日后做起生意来也不愁。
想到这儿,贾逊跨进木槛时兴致颇高,难得亲切道:「许久不见先生,今日路过偶闻先生喜得新观,恭喜恭喜呀。」
可那窗边人却不似他一般热情,临窗侧眸时只是微微向他颔首,道:「大公子。坐。」
贾逊听着他这不咸不淡的语气琢磨不出什么来,笑意稍僵,转念一想这承平道是叶氏的人,一定听闻自己两头倒的事情,不高兴也正常,这下心里头舒坦许多,坐下时将金冠扶正了,寒暄道:「先生近来……」
此时正值晌午,李意卿并未落座,只站在窗前,目光比他高一些,就这么顺着淌进小窗的碎日缓缓而来。
逆着光,贾逊看不清他的神色,却无端觉得有些心虚,半张着嘴没法合上,只能硬着头皮把后半句补完了,「……可好啊……」
「听闻近来溟西的车马往阆京跑得勤,」李意卿垂眼看着他,「大公子知道其中缘由么?」
果然,这清也先生还真将这事放在了心上,眼下如此说,是在等着贾逊自己给自己搬台阶下。
贾逊也是生意上的老油条了,当即脸不红心不跳道:「哎,自然是知道了,一提起这事儿我心里头就苦。」说罢,他还皱眉装着苦样,继续道:「朝廷发话,圣旨都递到我府外头了,这……先生,眼下到底还是周朝。这……唉,您说,我哪敢不从啊?」
贾氏在溟西当了几十年的土皇帝,朝廷的话听过几回?他眼下说大周,说朝廷,实则是拿着这「正统」来压他的话。
「先生今日问我,是商道上的人没给您大人传过去?哎呀,这事儿办的……到底是我不仗义了,没跟您和叶大人讲清楚,眼下弄得我里外不是人。」贾逊眼下还不想与叶氏交恶,便叹着气道:「怪我,怪我。但我也不能不顾贾氏安慰,也为难的不行……叶大人不会埋怨我吧?」
李意卿眼皮微垂,也不知听没听贾逊方才的解释,只是说:「阆京三城粮仓亏空,民田又被踏得乱七八糟,眼下要是没有贾氏的接济,这些人怕都熬不过冬。」
贾逊觑着李意卿的神色,听了好话也不敢贸然回应。他从前和这清也先生做过几次生意,深知这人面和心黑的脾性,眼下不知在哪等着呢,便只说:「这真是谬赞了,先生大义,我不过是为了自家,凑巧行了桩善事。」
他这两句话可谓是把李意卿的路堵死了,这样一来,李意卿既不能以叶氏之名索要,又不能用大义来绑架他。贾逊笑着看他,这清也先生素来狡猾,贾逊在他这儿没少受过气,眼下好不容易捉到机会,正等着看他笑话。
李意卿却不急,只慢慢道:「贾氏过去收着溟西三州的税,可比阆京朝廷威风多了,听说从前张氏要嫁女,却被你们拒了?」他话音宁和如水,缓缓传进贾逊耳中,语气轻松得仿佛只是朋友间的谈天说笑,「那张氏早年睚眦必报,心眼比针眼还小,眼下他们登上了万阶座,竟还容得下大公子么?」
「先生这话说得不对。脸皮嘛,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贾逊挑眉笑道:「人之劣性如此,贪财好色,贪生怕死。如今刀尖都悬在脖子上了,从前那点恩恩怨怨算得上什么。」
贾逊见李意卿没说话,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心下稍松,继续道:「其实吧,这事儿说到底也不难。我和张枫什么交情,和叶大人又是什么交情?只要大人一句不满,我就立刻把阆
京的供应断了。朝廷没了我这层银子呀,军备呀,薄得和纸一样好戳,叶大人杀入阆京还不是易如反掌?」
他这话说得容易。若李意卿真照着贾逊所讲的做了,不仅要欠下贾氏一个人情,更是会和民心背道而驰。试想,阆京三城如今就靠着溟西的供应活,要是因着叶帘堂一句话就使得三城无粮可食,叶帘堂就算登上了万阶台也不能长久。
李意卿的目光再次落到贾逊身上,轻轻笑了一声,说:「还是大公子所谋深远。」
贾逊被他这一声笑弄得后背发凉,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守在门边的刀秋,稍稍向他移了移,错开李意卿的目光道:「本公子不过是个生意人,到底都是依着叶大人行事。」
「大公子善举,承平道都替三城百姓记下了。」说到这,李意卿顿了顿,继续道:「但南沙那边,还是要公子一个交代。」
听至此,贾逊心下了然,到底还是要靠他们贾氏。他好笑地看一眼李意卿,腹诽道:「一番话转来转去说了半天,最后还不是要靠本公子的银钱。清也啊清也,到底还是嫩了点,狐狸尾巴没藏好就露出来了。」
「哎,先生有所不知,本公子眼下没有可活动的银子了啊,都送出去了,但没一个人还,都把本公子当冤大头,也苦恼得很。」贾逊险些忍不住笑,说:「本公子上个月还拨了万两白银让商道动起来,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