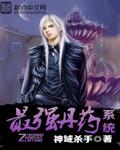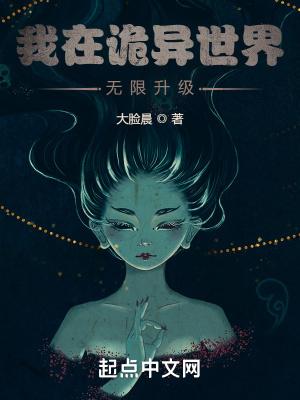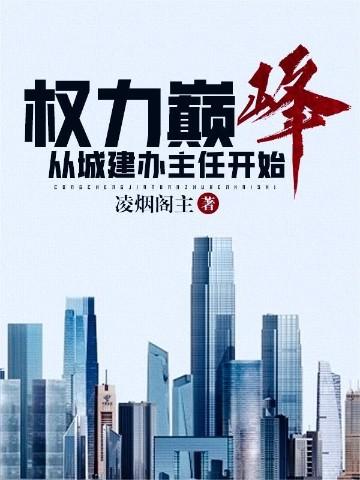我的书库>无极! > 第6章灵照(第2页)
第6章灵照(第2页)
“因为他知道,”老人望向窗外渐暗的天色,“有些规则,只有当人们真正害怕过,才会愿意遵守。”
当晚,伦理格物院召开紧急会议。苏砚清代表祖母提交了这份新发现的完整设计图及附注条款。全场震惊。原本主张全面封禁的农工代表开始动摇,支持科研自由的学者也被那三条铁律所震慑。争论持续到凌晨,最终达成折中决议:成立“梦引技术临时监管局”,试行顾氏三锁制,期限三年,期间每季度向社会公开审计报告。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有人赞其为“智慧的回归”,也有人讥讽“亡灵指路”。而在遥远的南极,“地鸣计划”实验室中,那位失明出身的首席科学家突然下令暂停所有数据采集。
“怎么了?”助手问。
他摘下耳机,额头渗汗:“刚才那一波共振……变了频率。不再是‘你还记得吗’,而是……‘他们听到了’。”
与此同时,东阳城纪念馆的“未来之墙”前,那个刻下“我可以不怕吗”的瘦弱男孩再次来访。他已经长高许多,穿着中学制服。老师告诉他,他的陶片已被选入“百年启封特别展”,还将录制一段语音存入无极档案库。
男孩站在麦克风前,沉默许久,终于开口:“十年前我问‘可以不怕吗’,是因为我怕说错话,怕被嘲笑,怕爸妈丢了工作。现在我还是怕,但我明白了??怕本身不是羞耻。真正可怕的是,习惯了不怕。当我看到学校悄悄恢复‘标准答案背诵赛’,看到新闻里有人说‘小孩子不该讨论政治’,我就知道,灯还没稳。我想告诉一百年后的你:如果你活得轻松自在,请替我们谢谢那些不肯闭嘴的人;如果你也在黑暗里,请记住,第一个说出‘我觉得,不该这样’的,可能就是你。”
录音结束,掌声悄然响起。角落里,一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默默摘下帽子,露出额角一道陈年烧伤疤痕。他曾是守序殿火焰队成员,亲手焚烧过上千册禁书。如今他是一名流浪教师,在各地乡村讲授“被抹去的历史”。没人认出他,但他清楚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本该点燃最后一捆书籍,却在翻开其中一本时,看到了扉页上一行铅笔字:“你也有权知道。”
那一刻,火把从他手中掉落。
此刻,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记下男孩的名字和话语,准备带回西部山区的课堂。他知道,有些种子不必立刻发芽,只要埋下去就好。
京都深处,林远坐在书房,面前摆着一份绝密情报:海外势力已在近地轨道部署“心智广播阵列”,可通过特定频段影响人类潜意识情绪。初步测试表明,暴露于该信号下的人群,攻击性降低百分之六十,但独立判断力同步下降百分之四十五。表面看是“和平促进工程”,实则是思想软控制。
他揉了揉太阳穴,提笔写下批示:“启动‘回声行动’??以同等频率反向发射‘疑问包’,内容取自全国中小学批判阅读课实录、街头辩论录像、监狱囚犯忏悔录、老兵战争反思日记……让他们也听听什么叫自由意志。”
笔尖顿了顿,他又补上一句:“附:请将顾怀瑾原始手稿第三卷解密,交由国家记忆馆公开展出。包括那句被涂黑的话。”
次日清晨,展览开启。众人涌进展厅,只见玻璃柜中,泛黄纸页上赫然写着:
>“真正的觉醒,不是从蒙昧到知晓,而是从顺从到怀疑。因此,我不怕世人无知,只怕人人‘明白’得太快??那往往是另一种洗脑。”
人群静默。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掏出笔记本,认真抄录下来。她不知道,就在同一时刻,火星轨道附近的自动飞船再次激活。能源仅剩3%,但它感知到一颗类地行星进入探测范围,随即启动预设程序,随机抽取一段音频播送出去。
那正是女孩昨夜参加校园辩论赛后,在日记中低语的一句话:
“也许我们都错了,但至少,是我们自己选的错。”
信号穿越亿万公里虚空,无声扩散。而在地球另一端,独臂老人顾怀瑾正教牧童用星轨计算季节。忽然,他停下动作,抬头望天。
“怎么了?”孩子问。
他没回答,只是将铜牌紧紧攥在掌心,仿佛听见了什么遥远的回音。
风又起了。
它掠过城市屋顶的太阳能板,滑过少年骑车飞驰的发梢,钻进图书馆敞开的窗户,吹动一页正在被人阅读的文字:
>“你可以不一样。”
然后,它继续前行,穿过山脉与海洋,奔向未知的远方。
就像那个永远不会停止的疑问??
“我觉得,不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