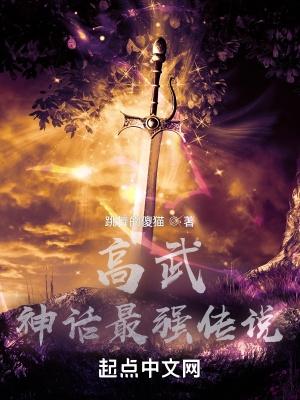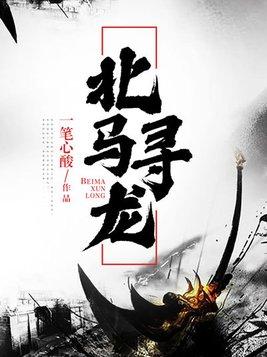我的书库>无极! > 第7章开荒(第3页)
第7章开荒(第3页)
>我怕梦都不是我的。
>我不怕说错话,
>我怕从此不再开口。
>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正常’了,
>那个问‘为什么’的人,
>是否就成了新的病人?
教室外,风穿过山隙,吹动一面残破的旗。旗面褪色,但仍可辨认出几个字:“岭南启蒙书院”。
而在遥远的牧区,顾怀瑾再次抬头。夜空清澈,银河横贯天际。牧童跑来,兴奋地指着北方:“先生,星星动了!”
老人眯起眼。他知道,那不是星辰移动,而是火星飞船在坠毁前的最后一道轨迹划过大气层。它带走了地球的声音,也将某个问题抛向宇宙:
我们能否永远保持发问的能力?
他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将铜牌放在石台上,任风吹拂。
几天后,苏砚清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音频。播放后,竟是她童年时的一段录音??五岁的她坐在奶奶膝上,稚声问:“奶奶,什么是自由?”
苏明昭的声音温柔响起:“就是你可以问这个问题,而不怕有人告诉你‘别胡思乱想’。”
录音结束,邮件正文只有一行字:
>“灯还没灭。我们在听着。”
她泪流满面。
当晚,她提交提案:将“顾氏三锁制”写入《心智科技基本法》,并设立“无极奖学金”,资助青少年开展独立思辨项目。议会辩论持续四十八小时,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
法案生效那夜,全国各地同步举行“静夜问答”活动。人们关掉灯光,在星空下围坐,轮流说出一个长久以来不敢问的问题。
在京都庭院,林远问:“我一生捍卫秩序,可我是否也曾成为压制自由的一部分?”
在边陲小镇,流浪教师问:“当我说‘历史不该被遗忘’时,我是不是也在强加我的记忆给下一代?”
在南极实验室,科学家摘下耳机,轻声问:“如果我看不见光,那我研究的,究竟是真相,还是我自己想象的世界?”
而在万千普通人家中,孩子问父母:“你们小时候,也像我们现在这样,连做梦都要考试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它们被录下,编号,存入“无极档案库”,等待百年后启封。
风依旧吹着。
它掠过沉睡的城市,穿过未关的窗,拂过一个少年枕边摊开的笔记本。纸上写着:
>“我觉得,不该这样。”
字迹尚显稚嫩,却坚定如初。
风托起这一页纸,让它轻轻翻动,如同一次无声的应答。
然后继续前行,奔向下一个疑问,下一次觉醒,下一段尚未书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