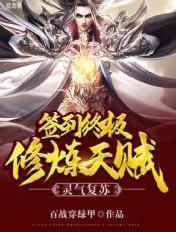我的书库>影视编辑器 > 第一百零九章 七把交椅(第2页)
第一百零九章 七把交椅(第2页)
苏宁看了他一眼,深知这位老臣的担忧所在,明确道:“方先生放心,内阁仅有建议权,即票拟”之权,而非决策之权。最终批红,用印之权,仍在朕手。所有奏章,未经朕之御览核准,不得下发。”
他顿了顿,语气不容置疑:“内阁,是朕的助手,是朕的智囊,但绝非分割皇权之机构。”
接着,他又抛出了另一个配套机构:“此外,朕身边还需一个更直接、更机要的办事班子,名曰“秘书室”。
这个名称更加直白,也更能体现其属性。
“秘书室之成员,皆由朕亲自挑选的年轻、精明、可靠的官员充任,不看重资历,只看重能力与忠诚。他们负责整理奏章摘要,传达朕之意旨、保管机密文书、跟进各项政令落实之进度,直接对联负责。
铁铉若有所思:“陛下,如此看来,秘书室更像是您的贴身文书与耳目?”
“可以这么理解。”苏宁点头,“内阁在外,负责初步梳理政务,提出方案;秘书室在内,贴身服务,确保朕之意志能准确、迅速地传达与执行。两者相辅相成,但核心在于,”
他加重了语气,“秘书室完全服务于朕,是朕意志的延伸,不受任何外界衙门掣肘。”
这一番布局,清晰地勾勒出苏宁心中理想的权力运行图景:内阁作为外脑,提供专业建议,分担琐碎事务;秘书室作为内廷手足,确保皇权指令的畅通无阻与绝对权威。
而最终的决策权,则被他牢牢地握在掌心。
通过这一系列精巧的制度设计,苏宁在推动波澜壮阔改革的同时,也将帝国的权柄,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中。
他深知,唯有大权在握,毫无顾忌,才能驾驭着大明这艘巨轮,冲破旧时代的迷雾,驶向他所规划的,那片广阔而崭新的未来。
天工元年,夏,南京。
新帝苏宁设立“内阁”的消息,如同在本就因新政而波澜四起的朝堂上,又投入了一块巨石。
文渊阁,这个昔日相对清冷的藏书之所,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大明权力场目光聚焦的中心。
皇帝明发上谕:内阁大学士七员,秩正五品,虽品级不高,却“待从左右,以备顾问,票拟章奏,参预机务”。
这“参预机务”四字,足以让所有嗅觉敏锐的官员心跳加速。
虽明言仅有“票拟”建议之权,但谁都知道,能日日接近天颜,能最先阅览天下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权力!
这七把文渊阁内的交椅,在众人眼中,已然成了通往帝国权力核心的七张通行券。
一时间,南京城内暗流汹涌。
各部院衙门、公卿府邸,拜访、宴饮、密谈骤然增多。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着野心、焦虑与计算的微妙气息。
清晨,吏部衙门口,准备入衙视事的吏部尚书张?d?n的轿子刚落,便被几位官员“恰好”围住。
“张部堂早!”“张大人,下官日前偶得一方古砚,知您雅好此道,特来请您品鉴。。。。。。”“部堂,关于今年南直隶官员考核之事,下官有些浅见。。。。。。”
张?面色平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他是掌管天下官员铨选的“天官”,在这内阁人选推举上,虽最终决定权在皇帝,但他的意见分量极重。
这几日,他府上的门槛几乎被踏破,各种或直白或隐晦的请托接踵而至。
他捋了捋胡须,打着官腔:“诸位同僚有心了。内阁人选,关乎国本,陛下圣心独断,自有考量。我等臣子,当以公心荐才,为国举贤,切不可存私念。”
几句话滴水不漏,既点明了关键在于“圣心独断”,又标榜了自己“出于公心”,将所有人的试探轻轻挡了回去。
兵部值房内,气氛则更为凝重。
兵部侍郎铁铉坐在主位,下首坐着几位同样出身军功或执掌要害的官员。
与文官们拐弯抹角不同,他们的谈话更为直接。
一位都督同知声音洪亮:“铁侍郎!陛下设内阁,参预机务,岂能尽是文人?难四年,方知兵马之重!如今虽天下初定,然北元残部犹在,边防乃头等大事!这内阁之中,必须有一位知兵事,晓军务之人!否则,如何确保
军国大事不被那些只会掉书袋的书生误判?”
另一人接口:“此言甚是!铁侍郎您深得陛下信任,又执掌兵部,于情于理,都应入阁!即便您谦逊,也当为我等武臣,为边关将士争得一席之地!”
铁铉默然不语,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