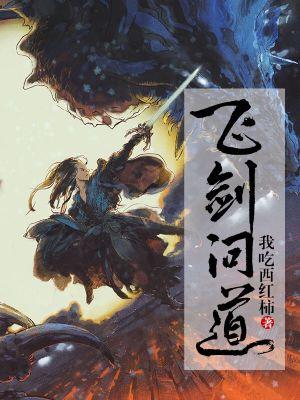我的书库>相国在上 > 243今日宜大胆(第1页)
243今日宜大胆(第1页)
杜氏将沈青鸾的反应看在眼里,心中既甜又酸,随即拿出一个同样用红绫包裹的帖子,递给张氏道:“此乃小女青鸾的庚帖,烦请官媒辛苦。”
张氏笑容满面地双手接过,高声唱道:“礼成!薛府纳采,沈府允诺!双方。。。
夜半三更,雁门关军营内烛火未熄。萧景珩披着玄色大氅立于帐中,案前摊开的不仅是北疆舆图,更有一卷泛黄帛书??那是先帝亲笔所书《边策要略》,其中夹着一页残破密笺,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北狄可和不可信,裴氏通敌之证藏于‘青梧旧邸’地窖第三层暗格,以松木为引,火漆封缄。”
此信出自已故老御史沈崇之手,乃其临终前托付族侄沈砚的遗言。而“青梧旧邸”,正是裴渊早年任礼部侍郎时在京郊购置的别院,后因扩建相国府被废弃多年,荒草丛生,无人问津。
“青梧……松木为引。”沈砚低声念道,眉头紧锁,“若真有此物,必是裴渊最不愿示人的罪证。他既敢私通外邦,定会毁迹灭证,怎会留存至今?”
萧景珩冷笑一声,指尖轻敲案角:“正因他认为早已销毁,才会疏忽。人心贪权恋位,越是隐秘之事,越舍不得彻底焚毁??或许只是一念之差,留下了一纸副本。”
他抬眼望向沈砚:“你父亲当年查办科场舞弊案,便是因追查一笔流向塞外的银款而遭贬谪。如今看来,那笔钱极可能就是裴渊用来收买北狄部落首领的‘安民费’。他们打着安抚边境的旗号,实则豢养敌军,待其壮大后再以‘平乱’之名邀功请赏。”
沈砚双拳紧握,眼中怒火翻涌。他终于明白,父亲一生清正,竟只是权臣棋盘上一枚被牺牲的卒子。
“我得回去。”他沉声道,“亲自去一趟青梧旧邸。”
萧景珩摇头:“太险。裴渊虽已被解权,但耳目仍在。你若擅自离营,必遭截杀。况且钦差身份敏感,一举一动皆受监视,贸然回京,无异于自投罗网。”
“那就让别人去。”沈砚眸光微闪,“谢大人在朝中经营多年,自有隐秘渠道。只需一封密信,便可安排心腹小吏假借修缮官舍之名进入旧邸勘察。只要找到那份火漆封缄,便足以将裴渊钉死在叛国柱上。”
萧景珩凝视良久,终点头:“好。但此事必须绝密,连谢韫也不能全知。我写一道手令,盖上玄甲令印,交由你亲信幕僚带回京城,面呈谢尚书。令中只说‘松枝重开花,旧屋见真章’,他自会明白。”
当夜,快马出关,蹄声隐没于寒雾之中。
三日后,京城骤雨倾盆。
谢府书房内,烛影摇曳。谢韫拆开那封暗纹密函,读罢久久不语,随即召来心腹家仆:“备车,去城西净业寺。”
“可是……雨势太大,老爷何必亲往?”
“此事关乎国运,也关乎生死。”谢韫披上蓑衣,声音低沉,“若今晚不去,明日或许就再没机会了。”
净业寺位于积水潭畔,原是前朝皇室香火院,如今香火寥落,唯余一位老僧守庙。谢韫踏入山门时,雨水顺着斗笠边缘滴落,在石阶上溅起细碎水花。
方丈室内,一人等候多时??大理寺少卿崔明远。
“东西拿到了?”谢韫开门见山。
崔明远从怀中取出一个油布包裹,双手递上:“按您吩咐,派人在青梧旧邸掘地三尺,终在东厢地窖发现一处夹墙。这便是从中取出的火漆匣,上面还有先帝年间兵部勘合印鉴。”
谢韫接过匣子,手指微微颤抖。他小心翼翼启开封泥,掀开盖板??里面赫然是一叠绢册与两封密信。一封用北狄文字书写,经译者辨认,内容为:“春雪化时,自雁门入,粮草备于赤岭,事成之后,割幽云十六州为盟。”另一封则是汉文,署名为“周延”,称已按“相国钧旨”将三千精甲伪装成流寇潜伏长城沿线,待北狄南下之际里应外合,制造边患混乱,以便裴渊再度掌权。
“铁证如山。”谢韫闭目长叹,“裴渊不只是结党营私,他是要卖国求荣!”
崔明远咬牙道:“眼下圣旨已夺其摄政权,但他仍居相位,门生遍布六部。若贸然呈报,恐反被其党羽搅乱证据,甚至诬陷我们伪造文书。”
“所以不能走寻常奏对之路。”谢韫睁开眼,目光如电,“我要以‘风闻奏事’之权,联合都察院十三道御史联名上本,直接请求陛下开启‘金殿质询’大典。”
“金殿质询”乃大胤祖制,唯有涉及谋逆重罪且证据确凿者方可启动。一旦举行,被告须亲临紫宸殿当面对质,百官共审,司礼监录供,皇帝亲裁。若罪成立,无需三法司复核,当场即可收押问斩。
“可陛下如今体弱多病,裴渊又曾掌控御膳房近十年……”崔明远迟疑,“万一陛下有个闪失,朝局将彻底失控。”
谢韫缓缓站起,走到窗前推开木棂。雨幕中,远处宫墙巍峨,灯火昏黄。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他轻声道,“但有些事,明知危险也必须做。十年前松溪畔,萧景珩替我挡刀;今日,轮到我为江山社稷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