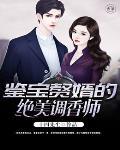我的书库>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583章顾政南离开了(第2页)
第583章顾政南离开了(第2页)
“但我们不会退。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坚持上学的女孩,都是在向整个体系宣战。她们不是在为自己一个人读书,她们是在为所有沉默的女儿、姐妹、母亲发声。”
她忽然笑了,温柔而坚定。
“前几天,有个小女孩问我:‘老师,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女孩子上学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说:‘会的,只要你不停下脚步。’”
她看向镜头,仿佛穿越千山万水,望进每一个正在挣扎的灵魂。
“所以今天,我不只是来演讲的。我是来请求的。”
全场屏息。
“我请求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偏远地区女童教育危机,支持‘姐妹微校’项目扩展;我请求各国政府加大对性别歧视文化的审查与干预力度;我请求媒体不再将这类问题简化为‘贫困’或‘落后’,而是正视其背后的结构性压迫;我请求每一位在座的你,若听到有人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请大声反驳??因为这句话,已经害死了太多人。”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最后,请允许我念一段查木乡孩子们写的诗。这是她们在学会拼音后,集体创作的第一首作品。”
她展开一页练习纸,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地读:
>“风吹走帐篷,
>雪埋住小路,
>可我们still来上学。
>因为我们want自由,
>我们need知识,
>我们are未来的light。
>老师说,我们不是burden,
>我们是star。
>所以,请不要stop我们发光。”
念完,她静静站在台上,任泪水滑落。
良久,全场起立,掌声如潮水奔涌,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外交官们红了眼眶,记者们放下相机抹泪,NGO代表纷纷走上前来拥抱她。一位非洲女权领袖拉着她的手说:“你在替全世界受苦的女孩说话。”
峰会结束后,BBC、CNN、法新社争相采访。“**Chinesewomanwhobroughtlighttothefrozenvalley**”成为热搜词条。日内瓦街头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尼玛次仁描摹“自由”二字的画面,配文:“**Themostdangerouswordinapatriarchalworld。**”
而此时,查木乡的新光小学教室里,十五个女孩正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卫星直播中的卓玛。她们穿着整齐的校服,胸前别着雪山莲徽章,眼睛亮得像星星。
尼玛次仁握紧拳头,低声说:“那是我们的老师。”
旁边一个小女孩突然举手:“老师说过,谁学会了写字,就能把自己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我现在会写‘梦想’了,我能告诉瑞士的小朋友,我也想当科学家吗?”
全班哄笑,又齐声回答:“当然能!”
与此同时,江倩倩在北京接到紧急消息:国家教育部联合妇联启动“雪莲计划”试点工程,首批专项资金两千万拨付至西部五省,用于建设一百所女子微型学校,并设立“反童婚快速响应机制”。文件批示栏上赫然写着:“**参照查木乡模式,全域推广。**”
李岩在营地收到通知时,正带着学生们安装新运来的太阳能板。他抬头看了看天,蓝天如洗,阳光洒在崭新的旗杆上,那面绘有雪鸽的白蓝旗帜迎风招展。
达瓦央宗翻阅着刚刚打印出来的政策文件,眼泪滴在纸上。她想起三年前,自己还是个躲在宿舍哭诉“什么都做不了”的实习生。如今,她已是“姐妹微校”项目总协调人,带领三十多人的团队穿梭于高原村落之间。
张晓芸则刚刚结束一场手术直播培训。通过卫星连线,她指导村医扎西顿珠完成了查木乡历史上第一例规范化剖宫产。婴儿啼哭响起那一刻,整个卫生所沸腾了。那个曾被认为“前世造孽”的产妇,抱着健康的孩子嚎啕大哭:“原来活着生孩子,是真的!”
当晚,营地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他们点燃篝火,升起孔明灯,每一盏都写着一个女孩的愿望:
“我想当医生。”
“我想考上北大。”
“我想让妈妈不再害怕签字。”
“我想让妹妹不用结婚。”
尼玛次仁的灯飞得最高。上面只有一行字:“**卓玛老师,等你回来,我要给你看我会写多少个新词。**”
千里之外的日内瓦,卓玛并未停留太久。演讲结束第二天,她便踏上归途。飞机降落成都双流机场时,迎接她的是自治区领导、教育厅负责人,以及一群举着横幅的大学生志愿者。